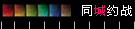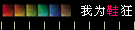英年早逝的王小波有一句经典的诗句,也可能是他一生惟一留下的一句诗。“我走在天上/而阴茎倒垂下来。”他发出这样的感叹是说:即便是一个在天堂里裸奔的神仙,也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她的妻子李银河阿姨是性学博士,对此也做了证明。
因此作为男人,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无能。在国力赛季末都输得找不见回家路的时候,还会用陕骂来发泄自己的郁闷。但是活着总是最重要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死的很伟大
。
安馨园在中甲的初夜是含蓄的,是简陋的,是在门口贴了红纸就开始了漫漫长夜的意淫,五十九岁的胡之刚在安馨园仅仅只打了三场比赛,就驼着背离开了,连头都没有回,“这就是天命。”他喃喃自语感叹老天难为。卡洛斯曾经翻手来云,覆手生雨,在陕西是个比米卢还NB的人物。卡洛斯的神奇曾经有人认为可以与世界第八大奇迹同列;马科斯的神奇则很像巨人国里的小人创造的童话故事,一个丑陋的笨拙的在巴西连替补都碰不上的队员却在中国穿上了银靴。但是两个神奇的人物也有无奈的时候,当神奇的光环已褪,因为金钱,因为卡洛斯口中那些如祥林嫂一样的故事,安馨园还是“没了”,中国人很忌讳说“死”。
“殇”在新华字典上的意思是还未成年就死了。中国人另一种说法是提前到极乐的世界去享福。冯军弟在今年西安飘起第一场雪的那个夜晚铿锵地说:安馨园降级是好事,应当值得庆贺。因为我们至少已经逃离了足球这个大染缸。但是把“死”说成是喜事终究还是一种自慰的方式,因为死后绝没有天堂,天堂里没有中国足球的座位号,陕西足球更是如此。没有人在安馨园降级后还敲锣大鼓喝庆功酒,或许也有例外,肯定是他的敌人。但是再大的英雄也遭遇过气短,一如《英雄》中无名、残剑、高山、流水的死,是英雄,但还是死。
2004年12月24日的晚上,冯军弟用不能脱俗酩酊大醉的方式向中甲告别,他的语气根据酒精含量而成几何数字增长,然后豪迈地说:不是不想流,只是心不甘。“有朝一天老子去玩中超。”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冯军弟的醉话,可以听,却绝不能当真。但老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事后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绝对没有开玩笑,这是真的。话可以说,但是要做却很难。
我们为国力而“殇”,大抵是因为国力的假设消亡,西北狼在离开陕西这块草原之后,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可以饱餐避寒的草原。为安馨园而殇又为了什么?为了他灵魂和肉体的重新轮回?江洪面对球队的“死亡”说话很平静:面对的太多了,你就没有感觉了。在岁月之河里,像古龙的小说,每天每个地方都有人死去,或者降生,山这边是腐尸和白骨,山那边是大红烛和唢呐。
经商的人都很迷信。十年前,军人出生的李志民放弃了生意用掷硬币的方式落脚到了西安;十年后,他同样用赌博的方式离开了西安到了宁波。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帝,国力的这种离开有人猜测是带有一定的宿命性。
六年前,冯氏兄弟还被称为农民企业家的楷模,还不清楚球场是几亩几分地,一天,他在麻将桌上终于知道了贝克汉姆脚法的精妙,六年后,他们已经公开向中国足协叫板了,公然一个足球大鳄。
殇,对于足球,只是一种形式,就像抽烟,倒不是因为她可以解愁,而是你在抽烟的时候,已经无意中做出了解愁的姿态。
(继续关注下一篇《陕西足球十年殇》———《地殇》)记者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