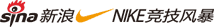八一乒乓球队断代史:从王涛到王皓 一时多少豪杰(2)
第一次,贺捷找到李振恃所在的上海邮电学校,一个叫杨永盛的老教练帮贺捷把李振恃的档案调出来,上面说李振恃的父亲是特务嫌疑犯,但经公安部门调查李父是清白的。又说他的舅舅是国民党的飞行大队长,炸过解放军,但李振恃连舅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根据第一次上海之行了解的情况,贺捷向八一队做了汇报。鲁挺当即拍板说:“这个人要了。”
第二次去上海,贺捷找到上海乒乓队的负责人余长春。余长春不点头,李振恃就不能走。“当时有个规定,只要是乒乓球人才,必须经过体委和乒乓队才能放出来。我们都是捡各省市队不要的运动员,训练成一流运动员。李振恃虽然没进上海队,但必须要通过乒乓球系统才能出来。”贺捷做余长春的工作:“你们又不用,再这么待两年就把这孩子坑了。”余长春同意盖了章,但上面不答应。
第三次贺捷没有直接出面,经过前两次那么一闹,上海体委和乒乓球队都知道贺捷这么个人。李振恃文革期间在空四军打过球,贺捷就出了个招,让空军乒乓球队以收回他为名要人。很快李振恃被送到沈阳军区,八一队再从沈阳空军把他调出来。李振恃那时的技术比别人高一块,很快就成了尖子。
贺捷说,八一队之所以长盛不衰,一靠队风纪律,二就是靠“明星”。被他挖来的“明星”还有铁道兵的施之皓、工程兵的戴丽丽、北京军区的童玲…… “我必须要挖到这些尖子,来带领队伍。”八一队先后出了11个世界冠军,有8个是经贺捷送到国家队的。过去乒乓球前三强是北京、广东、上海,慢慢地八一队的世界冠军人数就追上了上海。
贺捷重人才,但是有一条,靠关系进不来。当年郭沫若的秘书,要给贺捷一副郭沫若的字,让贺捷收下他儿子,贺捷说:“字不要,你来考试,合格了我再要。”因此在乒乓球圈,贺捷没少得罪人。“108将聚会的时候姜永宁和孙梅英的女儿跟我说:‘贺叔叔,当年你和我爸妈还是朋友呢,你都不要我。’我说不要你就对了,你现在是人才,但你不是打球的材料啊。”顿了顿,贺捷接着说:“不过我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叶佩琼的儿子李隼我就没留下。”
姚振绪坐专机下部队
姚振绪到八一队时已经26岁。跟别的队员不同,他是从国家队退役后才来的。1968年姚振绪从国家队回到上海,1972年在上海举行的球类运动会中拿了冠军,仍然是绝对的一号,但他并不被允许参加全国比赛,还被调走当教练。姚振绪不服,找上海体委理论,“让我当教练可以,但是太早了,我还可以打。”谈话总共五分钟,姚振绪拒绝了“安排”的工作,为此两个月没拿到工资。姚振绪先在海军打了两个月,随即参加了全军运动会,之后就进了八一队。“打球就得在北京,我在国家队待过我知道。”1973年在武汉的全国比赛,他在男团队伍中打二号,八一队最后拿亚军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没有国家队的也能打上来?第二次全国锦标赛李振恃没打,八一队又打了个第二。“没别的,就是靠拼!”姚振绪坐在位于东四块玉的家中,沏了杯茶,忆起当年,神情亢奋。
1973年,姚振绪在八一队是23级干部,最小的官,一个月6块钱津贴,不算特别高,但要比地方上好。“那个年代在部队地位高啊,穿军装多光荣啊。刚当海军时,军装下蓝上白,大盖帽和警察一样,我还记得有人找我问路。”
姚振绪离开八一队是在1975年,“1974年全国锦标赛之后,我的球不行了,顶不住了。”不久,姚振绪援外,但没脱军装,一直到1980年退伍转业,军装穿了8年。八一队的作风和纪律给这个“老兵”的印象最为深刻。“武汉全国锦标赛时,我们出去吃饭都排队去,只要一穿军装,就得一二一走。”
“那时强调老同志要带头,要以身作则。1975年我都28了,是年龄最大的。没人要求我跑多少,但我还必须跟大家一起跑,3000米11分半一点儿问题没有。这些是其他的地方没法比的,当过兵以后觉得没有什么苦吃不了的。” 现在,姚振绪还跟别人说:“你们孩子如果要打球,还是送八一队好。至少不学坏,对不对?”王皓的爸爸也对贺捷说过:“把孩子送到八一队我放心,不成材也成人。”
关于八一队,姚振绪还有另外一番记忆。在武汉拿了男团亚军后,八一乒乓球队经常下连队打表演赛。在那个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的年代,文体工作者慰问表演是家常便饭。姚振绪记得他们除了部队还去工厂和人民公社,有礼堂的在礼堂打,没有就在户外打。最夸张的一次是在福建前线,对面就是台湾海峡,在山头上打,风一吹,球滚下去就没了。姚振绪还记得,他和队友坐过军区司令员的那种十几个人的专机下部队去。
“现在郭跃华和陈新华的表演,什么转圈啦,我们那时候都打过,一点儿不比他们差。”那时姚振绪和队友们上过北京好多的舞台,一个球打完跳下舞台,下一个球之前再跳上去接着打。一次在中央党校打表演,舞台有两米多高,姚振绪跳了下去,再一看傻眼了,看不到球了。姚振绪拿手的还有“防空演习”,在对方把球打上案之前,从球桌底下钻过去接球。姚振绪在八一队练这个动作时是冬天,穿的绒衣绒裤,地滑一出溜就滑过去了。结果到了真正表演时,穿的短衣短裤,又是水泥地,一钻过去胳膊腿磨破了一大块。
乒乓队与足球队的战斗
事实上,早在1973年“特招”政策出台后,各军区代表队都在积极地招兵买马,实力并不在八一队之下。1979年上半年的全军运动会,几十支部队队伍齐聚红山口,有铁道兵、工程兵、空军、南京部队、北京部队、二炮、机械工程兵……最后铁道兵拿了男团冠军,贺捷看走眼的李隼,就是这个冠军队伍的一员。
李隼,1976年加入铁道兵体工队,1981年复员,1996年任国家队教练至今,王楠、张怡宁、李晓霞都出自他的门下。虽然没进过八一队,但李隼关于部队的很多记忆都与八一队有关。
在铁道兵体工队期间,李隼跟着部队上过青藏高原,坐着解放车到过新疆的阿拉山口,给铺铁路、修桥墩的战友打过下手……
1979年第4届全运会前夕,北京地区部队的体工队在红山口集训,李隼和李振恃住一个房间,他们的打法相同。李隼印象很深:“星期天李振恃拉着我踢足球,踢完后去乒乓馆练低球突击。你知道怎么练?拿着凳子坐在那发多球,一个人发二十分钟,我给他发完,他给我发,还教我。那功力,闭着眼睛也还能打过去。”那时李隼16岁,李振恃已经是世界冠军。
“那时候比较热闹,一到晚上就听施之皓的组合音响,一听能听一晚上。他从国家队带回来的。刚开始是一‘板儿砖’,后来变成了4个喇叭组合的那种。”
“我们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排球,身体训练跑完三千米,就等着排球队练完,他们一下场我们和足球队打比赛。就为了赌一瓶八一队的冰镇酸奶,瓷瓶的,那是八一队一绝。当时足球队的李富胜、付玉斌、王仁杰,三个守门员,都鱼跃跟我们打,我们都能赢他们。打完之后那酸奶正好冻得带冰碴儿,最好吃。”
夏天,李隼和队友到红山口前的运河里游泳,后来里面淹死过一个人,就不让游了。李隼就和队友去后山逮蛐蛐,一逮逮到半夜,“为了掐一蛐蛐,北方人能和上海人打起来。”在八一队军训时,一共14个人,7个上海人,“一开始打扑克,他们说话我们听不懂,老输。后来我们听懂了,把他们破译了,也不告诉他们。”
1979年全军运动会夺冠后,李隼在全军第一个破格提干。提干之前他的津贴是10块,提干后是15块。“提干后每礼拜回家,我自个儿坐332路到动物园老莫儿(莫斯科餐厅),叫上两菜一汤,那时没有超过1块钱的菜,一个红烩牛肉才几毛钱,一顿饭下来才2块多。”
1981年——盛世
“千万富翁”范长茂
1980年,范长茂到了八一队,在下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取得了自己第一个全国冠军,挣了120块钱,那年他17岁。
来八一队之前,范长茂在二炮打了三年球。“我从小就喜欢当兵,我父母更那什么,觉得军人家庭特光荣。”
网友评论
更多关于 王皓 的新闻
- 燕赵都市报:假如王皓“直通”掉队 2010-2-8 1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