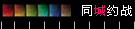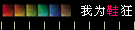特约记者贾知若北京报道 冠军来得迟了些,但常昊的“第七次”终以摆脱了苦难,成为丰碑式的胜利,这比什么都重要。
观战室:落寞崔父,忙碌张璇
崔哲瀚的父亲崔德淳一直坐在观战室里,不过他像个陀螺般转个不停,一忽儿坐在
韩国团桌上看小棋手们拆棋,一忽儿又走到网络转播室,搜寻一些有关棋局的更高级判断。
崔德淳也住在昆仑饭店,他有陪同19岁儿子前往重大赛事现场的习惯,早些年不少中国记者就认识了他,那是农心杯三国擂台赛上,崔哲瀚三连胜一战成名,那时候崔父就到过北京,望子成龙其情也殷。并不是每个父亲都有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幸运,但崔德淳也有不适应的时候,那就是在观战室里,他时时被镜头所瞄准,看上去他还没有崔哲瀚那样的心理素质,因为他经常回房间躲开记者们的镜头。
比赛临近结束时,崔德淳有点着急,他甚至直直地站在网络转播室权甲龙七段的背后,静静地听电脑里传来的韩语解说。一局终了,中韩记者们不约而同地涌向对局室,涌向应明皓、王汝南、华以刚和张璇,观战室里只留下两条孤独的人影———那是权甲龙和崔德淳在默默地摆着棋局的官子进程。以儿子为荣的崔德淳,同时也在为儿子分担着失意与痛苦。
张璇不再紧张,在接受记者采访前,她表示要先给家人打个电话,第一声就是“妈”,然后上海话绵绵不绝。多年前,常昊的母亲也会到儿子的大赛现场助阵,她基本上看不懂围棋,总是不停地问周围的高手们“形势怎么样了”,就连一些熟识的记者也不放过。据一位上海记者透露,常昊的妈妈虽然这次未能亲自来到昆仑饭店,但她已委托另一位《新民晚报》的记者:这次她总是预感常昊能夺冠,待常昊夺冠后,一定在昆仑饭店宴请所有新闻媒体的朋友。曾经为儿子分担过六次世界亚军之痛的母亲,有太多理由解脱一次。
对局室:王谊奋力“抢救”崔哲瀚
对局室的大门轰然洞开。激动的人流立马填满了对局室的每一个空隙。数码相机和摄像机的闪光灯劈啪作响。
“不能再挤了!”一个快被夹成“照片”的老记不满地抱怨了一句。旁边另一老记仍在奋力挣扎着,“五年才挤这么一回,挤挤有什么关系嘛?”
年轻一点的记者冲锋在前,冒着“相片”的危险,老一点的只能在后面颠簸,他们有时间相互交流一下———“这次为什么想采访围棋?”
崔哲瀚很苦,因为他被围在垓下,而且一直听中文的采访。他差点走不出对局室,大约有
10分钟,他在对局室的人山人海里茫然地听说采访常昊的中文版,直到王谊五段看不下去,才千辛万苦地在人堆里开辟出一条“路”来。崔哲瀚脸上挂着一点笑容,但显得有点惨然,走到一个僻静处,他一回头,却还是跟踪而至的摄影镜头,少年把头别向墙壁,愣了一愣,他似乎是想等自己的父亲出来,但崔德淳迟迟未至,于是,
19岁的崔哲瀚选择了独自一人提前离开,他的步伐越来越快……
讲棋厅:每个停顿都掌声如雷
讲棋大厅像个蒸笼,有趣的是,人群中掂起脚伸长了脖子的,竟然还有李昌镐的弟弟李英镐!而这一刻站在台上的人都充满羡慕,李劫四段就是其中之一,当一位记者笑着问他“你有这一天吗”时,他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台上的常昊,神往地回答“但愿”……
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多分钟,胆大敢言的聂卫平举着最后一张棋谱大声宣布:“常昊赢定了。”会议厅里第一次响起长久的掌声。几分钟后,从赛场的各个角落都传出了掌声。更多的人闻讯赶来,只能挤在走道上,大声要求主持人徐莹请出常昊和棋迷们见面。
灰西装、白衬衣的常昊从对局室后门溜上讲台,他的左边站着应明皓先生,右边正是他的恩师聂卫平。“谢谢,真的太感谢大家了。”常昊深深地鞠躬。“这个冠军来得晚了一些,但毕竟还是来了。我为去世的应昌期老先生还了心愿,为老师报了十六年的一箭之仇。”
每一句话之间的停顿总是迎来掌声如雷。兴奋的老聂挥着手“训徒”:“努力!咱们还差得远呢!必须大大地努力才行!”
还有一个人像常昊一样幸运。那个精确解答了问题的年仅8岁却拥有业余五段段位的小男孩得到了一把应氏冠军签名的折扇,折扇上早早题写了曹徐刘李的大名,在昨天终于添上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常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