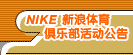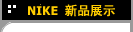| 足球周报:历史 从无到有或一念之差 |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2年12月27日03:08 足球周报 | ||
|
阿里·哈恩不算姗姗来迟,但却是迎着数亿中国球迷恐惧和躁动的目光而来的。 哈恩·汗或汉,一个幼稚但未必无聊的话题了,中国足球的一个新的历史轮回从哈恩的到来开始,已经勿庸置疑了。 他到底应该叫阿里·哈恩,还是叫阿里·汗或阿里·汉,似乎只是所有问题中的一个 2000年,我去悉尼采访奥运会。当地的华文报纸都把这座城市称作“雪梨”。我觉得“雪梨”的名字比“悉尼”要美得多,更贴近这座城市的风貌,甚至在往回发稿时都情不自禁地打过好几回“雪梨”两个字。 现在,哈恩可能只是一个我们对外国人名字的通常译法,而汗或汉可能更容易衍生出汉字的另类意义,例如他能否成为中国足球的一代君王或他能否被中国足球所“汉”化。 但这些在一切都未发生之前,都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阿里·哈恩能否把中国足球带进2006年德国世界杯? 足协与哈恩的合同就是这么写的。 哈恩·汗或汉,一个幼稚但未必无聊的话题。 对哈恩的信任与不信任,怀疑与不怀疑,都是牵强和附会,都是附庸和派生,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尽管这个时间可能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倒计时的轨道。 足协签下哈恩,尽管可能会有一份它的制约条款、它出台的严谨和足以保证的主动性却是与历届外籍主教练所签下的合同中最好的、最成功的合同,但合同本身之外所告诉中国球迷的前景却是不容乐观的,甚至是相当模糊的。 米卢在哈恩之前所创造的成就在中国球迷的眼中几乎是不可逾越的,虽然他的“快乐足球”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结束之后受到了广泛的批判与全面的否定,但历史性地冲进世界杯的事实本身就是一座丰碑,而这座丰碑在过往的中国足球历史中一直是可望不可即的。 在度过了对施拉普纳的顶礼膜拜和对霍顿的理论信仰以及对米卢的神奇幻想之后,哈恩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来到了中国,显赫的球员生涯与失败的执教经历注定了他要生活在中国球迷怀疑的视线里,而现在我们惟一可以信赖的只剩下这份合同中的冒险与运气成分。 孔子的学生子贡问老师:“您认为您的学生子张和子夏相比,谁更强一些呢?” 孔子回答说:“子张做事总是有所超过;子夏做事却往往有所不及。” “那么,一定是子张比子夏强些吧?”子贡问先生。 孔子摇了摇头,说:“过分与不及是一样的。” 对哈恩的信任与不信任,怀疑与不怀疑,都是牵强和附会,都是附庸和派生,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尽管这个时间可能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倒计时的轨道。 孔子学琴,从学谱到技法,从技法到情感,从情感到作者,精而再求精;中国足球从起步到风格,从风格到理念,从理念到规律,知表不知里。 孔子向师襄学琴,一支曲子练了十来天。 师襄对孔子说:“这支曲子你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可以学下一支了。” 孔子说:“还没有,我还只学会谱子,没有掌握其技法呢!” 过了些时,师襄又对孔子说:“你的技法已经掌握了,这回该学下一支了吧?” 孔子回答说:“我还没有体会到曲子的感情呢!” 又练了一段时间,师襄决定开始教孔子下一支曲子。这个时候孔子仍极认真地告诉师襄“我还没弄清楚这支曲子是谁作的呢!” 一个月后,孔子才兴奋地对师襄说:“我已经从曲子里了解到作者的为人:黑黑的面孔,高高的身材,两眼仰望远方,一心想以德服人,感化四方……除了文王,还有谁呢?” 师襄听了,惊喜地对孔子说:“你说得对呀。我记者老师曾对我说过,这支曲子的名字就叫做《文王操》啊!” 中国足球,其实也与孔子学琴一样的道理,可惜却没有一样的态度。 孔子学琴,从学谱到技法,从技法到情感,从情感到作者,精而再求精;中国足球,从起步到风格,从风格到理念,从理念到规律,知表不知里。 耳不论已经成为过眼云烟的施大爷和霍师傅,就米卢和哈恩的选择而言,就纯粹是两个极端的选择。 一个出身欧洲,流浪中北美,兼收并蓄、厚积薄发的神奇大师与一个在欧洲根深蒂固,却又碌碌无为的荷兰飞人,这种尼亚加拉瀑布式的落差使我们怀疑,哈恩与中国足球的互融性与互补性在哪里呢?仅仅凭着希丁克在韩国的成功就奢望荷兰攻势足球让中国足球一夜之间飞黄腾达,仅仅因为特鲁西埃与足协的不合作态度就摈弃既定的目标取向,同样,仅仅像南勇所说的合同上的制约条款就是中国足球未来一个历史轮回的全部选择吗?在这个前提下,任何有关哈恩职业素质、人品、合作态度的认同依然是苍白的。 历史可以从无到有地创造,但历史也往往系于一念之差。我们对于中国足球未来又一个轮回的担忧不无理由。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有句名言:“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当时若是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不同的。” 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是什么样,我们不甚了了,但至少哈恩的历史我们是知道的,“后米卢时代”的开始其实也是更确切的“哈恩时代”的开始。 一个新的“哈恩时代”的开始,必将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当这个历史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时,我们必须追寻历史的足迹,尊重历史的选择,驾驭历史的纵横。 1948年初,在苏南分裂前夕,以南斯拉夫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名列“四巨头”的米洛凡·吉拉斯为首的代表团曾应邀访苏。13年后,吉拉斯在其回忆录《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追述他与斯大林同车赴宴的情况时,谈到自己突然“一掠而过”地萌生了“假如现在有一颗炸弹在我们中间爆炸,把我们全都炸成粉碎,那将是一件多么震憾人心的大事变”的想法。 尼克松时代的白宫核心决策人物之一、国内事务首席顾问约翰·埃利希曼在总统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准备对他丢车保帅之际,心烦意乱的埃利希曼在与尼克松同机时,“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顾一切地扑向控制装置,把我自己置于飞行员的操纵杆和飞行员之间,那么我就会使每个人的烦恼从此烟消云散了。”8年后,埃利希曼在其回忆录《权力的见证》中描述了他当时的心理活动。 倘若吉拉斯或埃利希曼的念头付诸实施并得以成功,无疑会在世界上引起爆炸性的事果——不论从“爆炸性”一词的本义,还是从其引申义上都是如此,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甚至可能是无法估量的。 相对而言,足球是渺小的,尽管它是和平时代的战争,它以大众竞技性和娱乐性而成为世界第一运动,但它的存在和发展的的确确记载着一段历史。历史的轮回则告诉我们:它的变革或创造成功或失败往往就是系于一念之差。 哈恩的入主中国足球,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中国人的一种还没结婚就想离婚的可笑念头,准确地说,是一种可笑的思维方式,就像注定要有一个新任主教练到来一样,新一任主教练注定要被怀疑,甚至要被恐惧,要被躁动,中国足球的苛刻已经近乎变态,所以,“米卢”已经不是“博拉”了,而哈恩只不过是一张铺开的白纸,对他的任何涂画都有道理。当然,足协最希望得到的是“怎样为新主教练创造好的工作条件,让他充分发挥潜能,而不是天天在他屁股后而拿一把刀追着。”南勇如果说。 李·哈维·奥斯瓦德,一个24岁的枪手通过结束约翰·肯尼迪总统的性命剥夺了他继续创造历史的使命,也改善了林登·约翰逊参与创造历史的命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60年代以后的历史。 哈恩无疑将成为中国足球一个历史轮回的缩影,他很可能是中国足球一念之差的产物。他的成败与否,肯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足球的未来走势。 在期待哈恩成功的同时,我们无法掩饰担忧的理由。因为米卢率领中国足球创造了历史之后,我们的历史负重感反而更加坚现之后,中国足球除了沉重,还是沉重,沉重在目标的遥远之下,沉重在舆论的苛求之下,沉重在公众的不屑之下。 这可能是哈恩所始料未及的,而中国足球可以考虑未来四年的利益,却未必会考虑未来八年,十年的利益。最可怕的是,对于中国足球未来建设的保障措施却没有任何具有建设性的东西。(本报记者巴家伟)
|
| 首页 ● 天气预报 ● 新闻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
|
|
|
|
| | |||||||||||||||||||||||||||||||||||||||
|
关键词一 关键词二 | |||||||||||||||||||||||||||||||||||||||
| |||||||||||||||||||||||||||||||||||||||
| |||||||||||||||||||||||||||||||||||||||
| |||||||||||||||||||||||||||||||||||||||
行业信息高速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