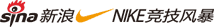南方都市报:纳达尔 当撕裂者被撕裂(2)


他使用了“感觉”这样的词,字面上来看,应该有感情、知觉、决断等等的意思,但如果把握网球拍这样的事排除在外,其实是非常荒谬的。高水平的网球比赛中的击球就像界于拳击与打棒球之间,击多重、击多高、球拍的角度、风的速度、场地的类型、球的旋转、对手的弱点、思想的变化等等。我在想,当纳达尔握着网球拍的时候,他是如何调动左手的感觉的?
“这是我惟一用左手干的事。”他说,“虽然我吃饭的时候两只手都挺灵活,但如果让我用右手打球———我做不到,完全不会打,连贝尼托都能打败我。”
惟一执教过纳达尔的教练——— 这在网球中可是非常稀罕的事,更多的球员都习惯于随着排名的变化不断地更改自己的教练——— 是他的叔叔托尼·纳达尔。托尼是个冷漠的家伙,当纳达尔比赛时,电视镜头总是会拍到他戴着棒球帽和一副墨镜、两臂交叉在胸前的样子。在拉法和托尼无数的故事中,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早在几年前,托尼就曾公开表示,只要他一旦看见纳达尔在赛场上不好好控制自己的脾气(比如摔拍子、在底线骂骂咧咧、或者对观众怒吼),他们的师徒关系就会立刻结束,或者他再也不会帮纳达尔整理球包。
这个故事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不不,我可从来没给他下过最后通牒。”当我在三月的迈阿密比赛中碰到他时,托尼用西班牙语淡淡地说,“他自己知道他不应该去砸球拍,这就像他知道吃饭时点了什么东西都必须全部吃完,明白吗?两者是一样的,那些球拍也是要花钱的。”
托尼没说错,很久之前他就告诉纳达尔小心对待自己的网球鞋,不要在地上拖拖沓沓。而在几年前,当纳达尔的经纪人卡洛斯·科斯塔要求托尼阻止纳达尔在比赛前总喜欢狼吞虎咽地吃巧克力面包的坏习惯时,托尼也是扬起了眉毛对科斯塔说:“不,让他去胃痛好了,第二天他就不会再这样了。”
“这是一种尊重。”托尼跟我说,“让这些家伙明白世界围绕着他们转很容易,但我无法容忍拉法在成为一名优秀球员的同时,却是一个坏的榜样。最近有个教练问我,如果去问一个年轻球员的父亲,他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还是一个法网冠军,你猜他会怎么回答。我告诉他:‘你完全错了,你只有让一个球员成为一个有礼貌的人,他才更有机会去赢得法网冠军。教养会让他更容易去完成艰难的工作。”
天赋“倒转正手”被他发挥到极致
“就那个年纪而言,他每一个击球的强度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西古拉斯说,“你看他训练就会觉得非常吃惊,“每一个球都非常有力而且稳定,每一天,他都像是生命中最后一次那样在训练。”
纳达尔结实的双臂近几年来已经令无数人羡慕不已,而他的无袖上衣、固定住桀骜头发的发带、长及膝盖的短裤更已经成为他的标志,令他看上去像一个闲暇的冲浪爱好者。他的双臂和双腿,常常引来一些观察家恨不得对他进行解剖,以了解他到底如何具有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曾经与桑普拉斯、莎拉波娃等人合作过的教练罗伯特·兰斯道普发明了一个词汇:“倒转正手”,来形容纳达尔标志性的正手击打。那些在训练场边看纳达尔训练的人都喜欢看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动作:他的球拍似乎能将网球撕裂成两半,球飞向网前时就像一个旋转的炸弹,那威力不仅仅是可怕的速度,还有难以预知的着落地点和弹跳方向。“倒转”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落地后的状况,他的球不会像一般的击球那样弹跳到胸口的高度,而是仿佛突然涨了气似的迅速蹿得更高———纳达尔每一次击球都会抡圆了手臂绕过头顶。
“他并不是惟一这样击球的选手。”兰斯道普说,“但纳达尔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他能在场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几乎对任何来球做出这个动作,并且得分。而且他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做到这一点了,而且谢天谢地的是,没有人告诉他:‘嘿,你不能总是这样正手击球!’”
纳达尔凶狠的正手上旋在三年前获得了量化,旧金山的一家网球研究机构用高速摄影机录下了纳达尔全力击球后球的旋转。“实际上我们研究了包括纳达尔、费德勒、桑普拉斯、阿加西等许多球员击球的旋转速率。”这家机构的一位研究人员扬戴尔跟我说,“桑普拉斯与阿加西的击球旋转大约在每分钟1800-1900转。费德勒的击球更惊人,达到了每分钟2700转。可是纳达尔呢?我们曾测得的最高数字是4900,而他的平均击球旋转率则在每分钟3200转!仔细想一想你就知道这有多可怕,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但就我来说,如果纳达尔以全力击一个球过来,我觉得我根本不可能看得清楚。”
托尼·纳达尔始终灌输给他侄子的东西是:每一分都要当作是最后一分——— 比赛的最后一分、每一天的最后一分、生命的最后一分。“这不仅仅是对这项运动的尊重,”托尼对我说,“如果你想做一件事,就必须尽全力去做好。在我们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父亲也没有教给我们,但你自己能看得到那种态度。拉法小的时候,当他赢得比赛第一分的时候,没有人会给他太多关注,而他会给自己打气,加油!那时比赛和训练一样,当他渐渐长大,他就会习惯了在训练中对待每一球,也会像在比赛中的最后一分一样。
麻烦:更快的速度,更大的问题
纳达尔的技术打法与他伤病之间的关系近几年来也都困扰着他,虽然并没有特别的研究成果支持这一观点,但当你看他比赛直觉就是——— 那很容易让身体受伤。这个家伙总是太努力地击球,无论在何种级别的比赛中。
“更快的速度,更大的问题。”纳达尔的医生安古洛·科陶洛这样跟我说,在纳达尔法网失利后,我在巴塞罗那与他见了面,“最近几年,网球运动改变了很多。我们已经习惯于谈论伤病:肘、肩、腕。但近几年,随着装备材料的改变——— 最主要是球拍,也包括拍线———我们也发现了许多新的伤病类型。每一样东西都在变得更快,所以击球也要求更大力和更快速,所以这也给双膝、脊椎甚至臀部带来了更多问题。”
说实话,纳达尔近年的伤病问题并不比其他许多职业球员更令人印象深刻:左脚的应力性骨折、球场外的一次肘部摔伤、膝关节不时的疼痛、肌腱炎。人们以为他疯狂的正手必须给肩膀带来麻烦,但至少目前还没有。“多年来我们一直做足预防措施———赛前和赛后都会进行力量或是耐力性的训练与恢复。”科陶洛说,“但拉法从来不会像人们想的那样让双肩承担过多工作,它们天生就是那样。如果你看看他的家人,你会发现他们全都一样的强壮有力。”(这是事实,虽然已经40多岁,托尼和米格尔·安古洛看上去仍像美式橄榄球运动员。”)
毫无疑问,相比泥地和草地,硬地球场对身体——— 关节、肌腱——— 的伤害要更大。而纳达尔越努力地想维持他世界第一的排名和集齐四大满贯的荣誉,他就越需要不仅仅是在泥地、更要在像包括美网这样的硬地赛场上赢得胜利。现在纳达尔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他有义务让自己全力以赴地去赢得胜利。科陶洛说,有时连他自己都觉得痛苦,那种对于纳达尔既要保持健康又必须去赢得胜利的要求。“这是残忍的要求,认为他有义务去赢得胜利。”
补救的方法?科陶洛叹了口气,“肌腱炎非常难治,”他说,“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消除炎症和多休息。他现在正在休息,但对于像他这样的球员,‘休息’这个词并不真正存在。”
“他们三年前就这么说了,我不可能坚持太久。”纳达尔说,“但四年之后,我却比以前更好。那些话让我生气吗?不会,我已经厌倦了听到人们说我不可以像这个样子打球。最终,无论这样打球是令我胜利、失败或其他什么,都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只想打得更好,而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在你的头脑。”
当被瑞典人索德林击败后,纳达尔举行了一个没有笑容的赛后新闻发布会,随后就与他的团队立刻回了家,他想一个人呆着。他和女朋友、家人一起庆祝了自己的生日,这可是五年来的第一次。
梦想:一艘普通的船,
出海钓鱼
“甚至直至比赛快结束了,每个人都还在想,一定会发生什么,一定会的!”当我在法网的媒体工作室碰见鲍恩时,他跟我说,“就像我们看过的许多电影,约翰·韦恩在电影的最后一定不会死,只是这一次,那个骑兵没有回来。”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各路记者不断地用英语、西班牙语试图让他开口多谈一点东西。但很多时候,他的思绪似乎还停留在球场上。索德林曾被认为是个并不太难承受压力的选手,但在那一场比赛中却令人吃惊。(纳芙娜蒂诺娃在电视解说中禁不住大叫:索德林已经完全打疯了!)而纳达尔从第一盘起就表现得脚步沉重,观众们知道纳达尔会慢热,所以大家都在等待着像印第安维尔斯站对纳尔班迪安那样的熟悉大逆转。
“你们知道,我输了。”纳达尔说,用他并不常有的不友好的语气,“我输了,这就是我能说的。今天我没能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那些近距离观看了他比赛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而米格尔·安古洛·纳达尔———他在马洛卡的家中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了比赛———后来跟我说,从比赛一开始,他就知道纳达尔会遇到麻烦,这是一个运动员对另一个运动员的直觉。“就像有时你走上街发现天上都是乌云,你就会知道今天不会是个好天气。”安古洛说。
在纳达尔与索德林的比赛中,法国观众会朝纳达尔发出嘘声,他们有些幸灾乐祸地看到卫冕冠军就要输掉比赛。不过他们热爱费德勒,在他一走进球场时就拼命地朝他欢呼。费德勒轻松地在场上滑步、击球,而索德林却总是狼狈地从后场奔到前场。最终费德勒直落三盘赢得了胜利。让·保罗·罗瑟———已经退休的前法国国家队领队在赛后跟我说:“如果索德林打纳达尔那场也是这样,西班牙人不可能给他机会。而如果纳达尔能走进决赛,费德勒永远也不可能赢得法网。”
最重要的东西是你的头脑,就像纳达尔告诉我的。网球运动手册里都会这么告诉你,但也有更多的指南会告诉你如何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当最后一分结束,费德勒双膝跪地庆祝,我在想此时的纳达尔是坐在马洛卡家中的电视机前,还是像科斯塔猜测的,可能正在地中海某个朋友的游艇上钓鱼。纳达尔喜欢钓鱼,而且连这个也喜欢和人家比赛———他无法克制自己,总喜欢和朋友们比谁钓到了最大的一条。有一次我曾问他是否想像过自己结束网球生涯之后的生活,他说的第一个词就是“一艘船”。
他说他仍会住在马洛卡,他和他的妈妈目前正在筹备一个基金,旨在帮助提高发展中国家儿童的生活;他会在基金还有运动领域从事一些工作。“如果我的职业生涯还能持续三年,那我就再打三年。”他说,“我仍然想在网球上进一步提高,如果只能打两年,那就两年。如果五年或者更多,那就太棒了。”然后,他会买一艘船,他说,并不是很大的那种。“一艘普通的船,”纳达尔说“在大海上钓鱼。”
文/辛西娅·戈内(CynthiaG orney)———《纽约时报》周日杂志版专栏作家,同时也在加州大学新闻系授课
编译/记者 窦俊
CFP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