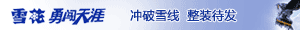江弋:球迷有理想 足球才有希望
本报评论员 江弋
想人生最苦是离别,唱到阳关,休唱三叠。
比赛都结束5分钟了,他们还在唱。0比4惨败、第一个打道回府,爱尔兰人并没有一脸悲凄愁苦,只用了一首歌的时间,他们就从输家变成了天使。
再弱小的民族都应该有属于自己心灵的歌谣。
《阿萨瑞原野》,爱尔兰古歌,内容与足球完全不沾边,它却是本届欧洲杯开赛至今“民间”奏响的最强音,当东欧赛场被斑驳的历史仇恨、民族对立、种族歧视乃至街头霸王压得喘不过气来之时,从满目绿色的看台传来的这阵歌声,犹如天籁、负离子、马蹄爽!爱尔兰人用自己歌喉唱出了一句无国界的真理——— 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这样的球迷真伟大。
爱尔兰球迷在为纯正的足球趣味歌唱,他们不分敌我,既为西班牙精灵喝彩,也为自己的笨拙、不放弃精神鼓掌,这样的歌声,本身就是足球情场最原始的为爱痴狂。
悲观的民族盛产哲学家,乐观的民族盛产艺术家。听罢《阿萨瑞原野》,你便容易理解爱尔兰国徽为什么会是把竖琴。视死如生,汉朝人的生死观到了爱尔兰人反抗英国殖民者时,就是一曲曲越挫越勇的琴声悠扬。
爱尔兰人像忠于自己的女人一样忠爱音乐。这个国家曾不允许离婚,但是可以选择婚期年限,1年的登记费折合人民币2万多,100年只要6元钱———与其说这是赚钱还不如说是一种美好的祝愿。法律都能浪漫到如此境界,难怪这里是肖邦夜曲的起点,贝多芬灵感的源泉;难怪这里有恩雅、酋长乐队和奥康纳;难怪这里能生出可儿家族合唱团,大哥吉他、大姐小提琴、二姐打鼓、小妹锡笛兼主唱———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纤尘不染的吹拉弹唱。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格但斯克的歌声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不是吊丝以貌似自我矮化的方式接受残酷的现实。歌声是爱尔兰人献给足球、献给球迷的风雅颂。凯尔特人的音乐是真正的世界音乐,全世界万难找出第二个国家像爱尔兰这般,能将最炫民族风和宗教的圣洁,浑然天成地唱响云端。
这样的音乐就像一杯加冰的百利甜,层层叠叠、有条不紊,奶油慢慢在威士忌中融化,巧克力尽情挑逗着你的舌尖。
“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迎接新的一天,一个人努力活下去……”青山七惠《一个人的好天气》仿佛在鼓励爱尔兰人继续唱下去,这次到双兰看球的外国球迷并不多,欧债危机之下,家家都不好过,c组四国平均每六人就有一人失业。格但斯克的看台上绿肥红瘦,爱尔兰球迷自嘲说:“西班牙球迷都忙着挣钱还债去了,我们反正已经失业了,就把这仅有的一点积蓄拿出来看球吧……”
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
十八世纪都柏林诗人汤麦斯·摩尔为民歌写下:“夏天里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它可爱的伴侣已凋谢死亡。再没有鲜花陪伴,映照它绯红脸庞,与它一同叹息悲伤”。即将失去爱尔兰球迷之歌的欧洲杯就是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花。
爱尔兰球迷的歌声让全世界的球迷敬仰、震撼,不是因为他们的歌喉歌技高不可攀,而是他们用歌声让球迷找到了与对手沟通的语言———人与人之间,还能在这样一个阴冷的雨天,如此心贴心地在创口中取暖。
把酒当歌,就让爱尔兰人主办2020年欧洲杯吧。
他们的歌声崇尚绿色,绿色就是生命和力量;他们的歌声饱含同情心,一个40%的家庭都养狗的国家,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他们的歌声充满豁达,他们超脱了对自己脚下足球的小爱,到达了对体育精神的大爱。
在那阿萨瑞的原野上,球迷才有理想,足球才有希望。
|
|
|
相关专题:2012欧洲杯专题 |欧洲杯西班牙VS爱尔兰专题
更多关于 欧洲杯 的新闻
- 东方早报:欧洲杯好久不见坏蛋 2012-6-16 06:30
- 旺仔:欧洲杯B组出线形势解析 2012-6-15 15:27
- 大连日报:欧洲杯盛宴之上不应有杂音 2012-6-15 13:01
- 长沙晚报:今年欧洲杯不收礼 2012-6-15 12:28
- 长江日报:欧洲杯大家一起数星星 2012-6-15 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