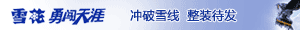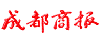江弋:欧洲杯该如何面对仇恨
本报评论员 江弋
“俄罗斯打波兰,德国人当裁判,卡廷森林就在眼前。”
俄波大战前我发了这条微博,看上去很有意思,至少波兰同行也是这么干的:波兰《新闻周刊》将国家队主帅斯穆达p成了抗苏民族英雄毕苏斯基的形象放在头版显著位置,还辅以波兰军队的座右铭:忠诚、家园和祖国。
这究竟是一场足球比赛,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人们总是可以创造出某种体系使原本毫无联系的东西产生出合理的联系”,安贝托·艾柯在《过度诠释文本》中这样提醒我们———我们是否都在不知不觉中过度诠释了足球?
英德大战=《大不列颠上空的鹰》、荷德大战=《遥远的桥》、英法大战=《圣女贞德》、德法大战=《西线无战事》,当战争成为历史的人质,足球就成为了仇恨的俘虏。
欧洲,尤其是东欧的仇恨有多诡谲,下面这个笑话可以一览无余:前苏联时期,一名听众打电话到“亚美尼亚广播电台”问了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预测未来?”得到的答复是:“当然,没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未来,可我们的问题在于过去,他老是变来变去……”
仇恨,就是一种变来变去,慌乱的不确定。
右耳听波兰人倾诉“保卫华沙”、“卡廷惨案”、“华沙起义”,你会觉得不揍俄国佬两拳不够兄弟,不够普世主义;可左耳又一听,俄国佬也有恨———约有12万~13万名苏维埃战俘于1919~1921年间被关押在波兰,“对俄国战俘的酷刑和侮辱令施暴的波军士兵都感到不寒而栗……”最终,有45000名俄国人死于集中营,图措拉死亡营———更被史学家认为是骇人听闻的奥斯维辛的“罪恶先驱”!
米歇尔斯说足球就是战争,可以理解,他手下的名将范哈内亨全家80%的亲人都在1940年的轰炸中丧生,包括他的父亲、姐姐和两个哥哥,所以“每一次面对德国队(微博)的时候,我就充满了仇恨。”
可是当今天基辅迪纳摩队的部分球迷在看台上挥舞纳粹旗帜,行纳粹军礼,仇恨顿时就让人费解,连德国记者安德雷亚斯都在自己的评论里这样寻求答案:“我的天啊,这怎么可能?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的爷爷辈,很多都是被纳粹杀害的吗?”
仇恨,没有生日,没有边界,没有上限,甚至没有原则,所以才在历史七嘴八舌的诠释中特别忙碌。
更危险的是,当这些掺杂着历史血迹、种族主义、民族情绪、政治倾向的仇恨注入足球,它已经完全颠覆了传统“足球流氓”的定义。足球流氓肇始于英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英格兰的灾难”,撒切尔夫人甚至成立了“作战内阁”来制定镇压足球流氓的对策……但这些基本只在球场内外、只在胜负、黑哨等“学术范畴”,多半要借酒精之力来滋事的流氓与昨晨我们见识的东欧足球流氓相比,简直是一部轻于鸿毛的《阿飞正传》。
足球该如何面对这些恐怖的新仇和沉重的旧恨?这取决于整个欧洲的态度。
美国学者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给出的态度是:二战后的欧洲是依靠人们对过去的遗忘而得以重建,1989年之后的欧洲则是在一种过度的回忆中再次重建———这两个欧洲的基石都不稳当。我们并不提倡一个民族健忘,但一个企图长久安定的社会,需要一定程度的忽略甚至遗忘。只有如此,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在奥斯维辛的焚尸炉上重建的欧洲是如此重要。
托尼·朱特在自己的杰作中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德劳内杯庆幸的观点———要说能把整个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欧盟,是足球。
健康的足球应该是全人类和平、互信、友爱、谅解的外交大使,而不是仇恨的泄欲工具。
|
|
|
相关专题:2012欧洲杯专题 |专题
更多关于 欧洲杯 的新闻
- 郭韬略:欧洲杯要清凉瞄看台 2012-6-14 12:16
- 深圳特区报:暴力欧洲杯难去的阴影 2012-6-14 10:48
- 吴向阳:欧洲杯足球流氓来了 2012-6-14 10:47
- 成都晚报:欧洲杯的舒克和贝塔 2012-6-14 10:42
- 徐霄杨:欧洲杯东风劫 2012-6-14 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