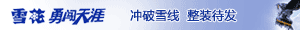龚晓跃:舍甫琴科老兵不死
龚晓跃
我要再不歌颂下安德列·舍甫琴科,我就不是一枚合格的老炮。
那天快天亮的时候,36岁的舍甫琴科用外科手术式空袭,在短短几分钟连下两城,率领乌克兰逆转瑞典。当舍甫琴科打进第二球,以一种从容而感恩的步调跑向60岁的布洛欣,两代基辅迪纳摩灵魂深情相拥,我问另一枚老炮:是不是有点要老泪纵横的意思?彼老炮憨厚地回复:是。
此老炮与彼老炮皆已进入人生下半场,要再去粉下谁,实在是很难做到的事情,特别是你发现年轻时追过的那些星,往往岁月掩不住他本来的傻逼,你就更难拿着一大把年纪去干出粉谁这种肉麻事体了。所以,这些年,我除了小粉粉我们自家兄弟、轴着一把不忍与无良牛奶作斗争的王小山,基本上是看见红人就退避三舍,怕被他们吓着。所谓混在当下,就是能自个儿把道理琢磨明白、不干坏事就功德无量了,但凡瞎起哄的事情,都得躲远点。
但是那天乌克兰打瑞典,比赛前我看乌克兰资讯,看到舍甫琴科的名字时,突然发现自己死水微澜般小小地激动了一下,这哥们是我年轻时最热爱的足球明星啊,我想起过去的好时光了。
昔年基辅迪纳摩血洗巴萨皇马,舍甫琴科如彗星般撞击欧陆,有着干净而忧郁的面容。我那会儿很得意的是,我发现这枚乌克兰的核弹头,长得多么像林青霞版的东方不败啊。舍甫琴科身上焕发出来的杀气,阴柔又决绝,甚至带点书卷气,呈现出上乘的审美愉悦感。事实上,当他加盟米兰,乔治·阿玛尼便发现,这位小兄弟是世界上穿阿玛尼西装最好看的男子。
当我怀念舍甫琴科,追忆似水年华,我想到的不是他迎风一刀斩的出击状态,而是他弥漫在赛场的气质,他不咋呼,他拥有那种安静的力量。
在那一场可歌可泣的比赛后,我听两位声称那一夜“不守到天亮不知道自己多幸福”的妹妹在那里抒情。一个说:我的神呵,回米兰吧。另一个说:不,就让他在基辅迪纳摩终老。我支持后一个妹妹。
与舍瓦同宗的乌克兰现代诗歌奠基人塔拉斯·舍甫琴科,曾经在他著名的《遗嘱》一诗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当我死后/请将我埋葬吧/在辽阔的乌克兰平原/我的墓碑高高竖立于/这田野,这无尽的草原/这第聂伯河,这峭壁。字里行间流露的诗人心境,与我们这里推崇的“老兵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家乡”如出一辙,堪称普世价值。
舍甫琴科不是斗兽场里的角斗士,足球远不是他的全部,他居住在看得见群山的科莫湖,就像安居于自己的内心,不妄不伪,低调而安宁。在那个功名的竞技场,他不必恋战,更无须强撑,他知道恋战强撑的那叫老不死。他依旧扮演征人的角色,是因为他心中有花,尚能开花,当韶华逝去,花开无期,他就回到了家乡。他讲述的是一个老兵不死的好故事。
这个充斥着“老不死”的烂世道,还能留给我们一个不死老兵的传奇,也算是一种恩典。
|
|
|
相关专题:2012欧洲杯专题 |专题
更多关于 欧洲杯 的新闻
- 东方早报:欧洲杯新晋头牌 2012-6-14 07:23
- 现代快报:欧洲杯流行思考人生 2012-6-14 07:14
- 申江服务导报:俄罗斯会成为欧洲杯大黑马? 2012-6-13 19:16
- 东体:欧洲杯的悬崖边逆袭 2012-6-13 16:30
- 东体:欧洲杯不玩预测 2012-6-13 1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