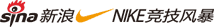葛爱平:我眼中的南勇杨一民
南、杨事发至今,各种传言不断,兴趣点更多都在追踪他们身在何方,甚至还有跳楼的报料,而我认为研究南、杨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怎样防止后人步其后尘,比追踪小道消息更重要。至今我仍在为那条“南、杨失踪”的消息震撼。因为南、杨留给我的个人印象,还真的很不错。相比之下,我对杨的认识更多一些。
那是1992年春天,中国足协牵手上海大众请来德国教练施拉普纳担任中国国足主教练。那天在国家体委训练局足球场上,施拉普纳主持第一堂训练课,那个著名的“豹子精神”就是这堂课上喊出来的。我留意到有一个戴眼镜的瘦弱书生,拿着笔记本站在场边一声不吭地记录。后来知道他叫杨一民,北京体院的研究生,是当时国家体委主任介绍过来专门记录老纳施教的方式,以备今后中国教练总结学习。
自此杨一民一直跟随着中国队担任场边文案工作,直到这届国家队结束。杨一民一直以学生的姿态待人,未言先笑,我对他的好印象就是从这开始。之后杨一民仕途顺利,一直做到足球管理中心副主任,但和善为人的风格一直没变。2005年他带国家队去韩国、澳门打东亚四强赛和东亚运动会。每回中国队比赛完,主教练朱广沪回房观看录像时,杨一民也会一旁作陪,时而插上一两句评点。老朱说,杨一民从不干涉他的工作,很少找他们开会。
2007年女足世界杯在中国举行,杨一民担任中国队的团长。看得出他和队伍很融洽,每回比赛队伍上车前,他都要站在车门口,嘻嘻哈哈地与队员一一击掌。和多曼斯基也配合得很好,记得他曾经和我说过:“我不会干涉她的工作,最多提一些建议,但听不听是她的事。”女足世界杯赛后,杨一民被换岗了。有一次在电话里我问他:“为什么女足打得不错你却换岗呢?”他回答说:“人家(指谢亚龙)都提了,我能说什么呢?”给我的感觉是,杨头的组织观念很强。
与南勇相识是在米卢的国家队时。之前听到不少的关于他硬的一面,包括怎么收服狡猾的老江湖米卢。我们之间很少有交流,保持着淡淡的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但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收到南勇发来的贺年短信,看得出他为人还是很细腻的。
2006年中国队在欧洲拉练比赛,有一次在早餐桌上我和南勇聊了一个多小时,那是我认识他以来,我们之间最长的一次对话。那天他似乎很想说什么,最敏感的话题是为什么选阿里·汉而不是法国人特鲁西埃,记得也是他主动提起的:“特鲁西埃开口要100万美金,要自带团队,还只对最高领导负责,这一点我们无法接受……不能冒这个险”。对于为什么选择阿里·汉,他则没说什么。
南勇带队的风格与杨一民相反,场下抓得很紧,经常组织教练组开会,并且总是要开到第二天凌晨。有一次国家队在苏州比赛。赛前训练结束的晚餐后他组织教练开会,到凌晨两点还没讲完,大家都困得受不了了。后来老朱也“忍无可忍”,索兴摊开图板,详细地把第二天的用兵布阵详详细细说开,“大家都别睡了……”老朱告诉我。会议开到凌晨3点多。
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得出,南、杨工作方式差异很大,但留给外界的印象都是很努力地想做好。但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把他们引向歧路。这是个什么力量?这是一种不被监督,不容质疑,无可阻止的行政权力,可以让坐在这些位置上的人飘飘然不知天下,从一个个理想青年和单纯学生,一直走进深渊。只不过是犯了众怒的中国足球,没有那么多耀眼的金牌庇佑罢了!
写下这篇文章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比起人的自觉性来说,有制约的制度更可靠。只有好的制度,才能制约住人性中存在的“恶”。南、杨的事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葛爱平)
网友评论
相关专题:中国足坛反赌风暴专题
- 中国新闻周刊:足球病人 体制造就了南勇 2010-1-27 11:00
- 金属:恶搞南勇专访 足协没有制造诡异比赛? 2010-1-27 10:11
- 大张鹏:1月5日那场是告别赛 为南勇的下场惋惜 2010-1-27 10:08
- 新华日报:靠什么保证不出“南勇第二”? 2010-1-26 16:18
- 丘志坚:南勇领国足用钱买出?看国脚明码标价 2010-1-26 1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