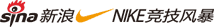《新闻晚报》孙文祥:中国足球 三生无耻
□晚报记者 孙文祥
一家地方报纸准备开设言论版块,担任编辑的朋友让我帮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找几个腕儿。让我沮丧的是,几圈皮条拉了下来,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接招,普遍的理由是: “一想到未来某天他们可能让我谈论中国足球,我就担忧自己半身不遂。”
麻木,的确是每个靠评论糊口的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敏感一点的读者或许已经留意到,自从时针走入2009年,我已经越来越少谈论中国足球。如果可能,我甚至希望自己的这个专栏,从此后不谈中国足球的风云,只讲世界体坛的风月。
谢亚龙离开后,我不是没有想过,中国足球在南勇的领导下,会变得清静一点,太平一点。但现在看来,这种想法若是被阿娇知道,估计又会被套上 “很傻很天真”的帽子。高洪波领军的国足,一离开范琦和万大雪的哨声,立即又与新加坡和大马杀得难解难分;而在中超,只要和国安有关的纠纷,你总能看到另一种判罚标准。比如同样是倒地后的报复,同样没有将对手的两个蛋蛋变成一个,李玮峰因禁赛远走他乡,而陶伟却能安然无恙。
有人因此认为,与其将足协当成国安的爷,不如说足协是国安的孙。国安在中超的份量,就像皇马之于西甲,法拉利之于F1。似乎在某些足协官员看来,一旦绿林军宣布退出,中超不仅会从凤凰变回乌鸡,甚至会沦落成野鸡。
既然一碗水不能端平,处罚就会失去它应有的威慑。带头围攻主裁的泰达主帅左树声,在面对停赛五场的处罚时,其若无其事,其大义凛然,简直能让人想到19世纪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从左树声到谭望嵩,再到以博尔特之势追打裁判的天津全运足球队,天津足球似乎想要证明,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倘若只是天津足球老老少少彪悍,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如今的中甲球队,也学会了东南亚老虎杯上的那些伎俩——在与四川智谷的比赛中,三球领先的青岛海利丰球员居然试图将皮球往自己门里踢。
按照正常逻辑,在一生二、二生三之后,应该是三生万物,将酒后驾车视若家常便饭的人,可能会在仰头喝下最后一杯前,向酒肉朋友高呼一声, “三生有幸!”然而,面对江河日下,人心不古的中国足球,我能想到的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耻。
身体的某个部位出了问题,还可以借助药物。若是中国足球让你不举,估计除了逃,也不会再有别的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