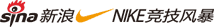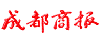成都商报:龚建平未动摇中国足坛潜规则
龚建平长眠于北京天寿陵园内一个略显寒碜的角落,他只活了44个春秋,一点也不“天寿”,这个陵园的名字之于他与他的那场雷阵雨之于中国足坛一样极不协调。“人垂泪天降雨天人共悲旷世奇案皆知晓”,五年前他的灵堂前有这样欲言又止的挽联,五年后,在花生米、卤肉饼这些祭品和几束神秘的鲜花面前,龚案的隐情依旧是隐情,人们记住的仅仅是一个纪录———十年徒刑,迄今仍是全世界裁判因受贿受到的最重惩罚,此前一名新加坡裁判因受贿8000美元被判了7年已经是破天荒。
五年后,陈培德认为龚建平是替罪羊,“判他不冤,但他太亏,他是我们现行体育体制下的悲剧人物。”我认为这是在不为龚翻案的前提下能作出的最公正评论。世人对中国足球的极度麻木或过度娱乐都让龚建平这个“标志性”的名字过早失去了应有的“弹性”,作为中国足球史上惟一被揪出来并判刑的黑哨,龚建平的悲剧在于,他这本曾经轰轰烈烈的“反面教材”在其身后的世界里,一点资治通鉴的价值都没有,酷似文革岁月里那些歇斯底里的口号标语。
龚建平这本“反面教材”,是自助的,是孤立的,是中国足坛在那一年的那几天中才需要的。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将中国从古到今的很多社会问题都归纳为“用一种道德上的情感替代法律应有的健全。”龚案就是这样。谁都知道他不应该是第一个被捕的裁判,更不是“假A假B”时代惟一收过黑钱的裁判,2001年12月31日,在一次由某门户网站发起的“最黑黑哨”评选活动中,龚建平得260分仅排在第16位,而高居榜首那位得分高达43900分。
属鼠的龚建平不是老实,而是有点懦弱和迂腐,他被报道的“堕落”细节平淡得犹如开水与白面包。他爱车如命,最风光时也就开得起一辆夏利;他好两口小酒,不是百龄坛而是红星二锅头;宋卫平给他几万块钱,他先买了樟脑丸,折叠得四四方方才放进衣柜;甚至到了2002年初足协内部开始清查的时候,他的智慧仍停留在———反正钱又不是我开口要的,现在又一分不少的退了,怕个X啊!
裁委会主任李冬生不久前在谈到龚案时斩钉截铁地表示:“在他之后,我们裁判的思想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有明显提高。”这其实不重要了,裁委会应该自问的是:在龚案后,裁判们偷偷上交调查组的黑钱累计达千万元,这样的“自首渠道”是否在践踏尽人皆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裁判圈最基本的、光明正大的规则?对每一个中国足球裁判而言,裁委会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而对俱乐部来说,裁委会的委派之责成了最大的暗箱操作,这一关系链条不禁让人会联想起明朝的司礼监,掌管几万名太监的荣辱生死,最终搞垮祖宗基业的痛史!
龚建平的案和死似乎没能动摇中国足坛根深蒂固的那些与裁判关联的潜规则,五年后,龚建平在地下应该感知,只有他自己的家被摧毁了,而中国足球圈暗流的围墙依旧密不透风。
(江弋)
网友评论
更多关于 龚建平 的新闻
- 成都商报:龚建平的悲剧 2009-7-19 03:47
- 明月彩云:网友五年再回首 发文悼念龚建平 2009-7-15 10:18
- 尹波:龚建平之死与扫黑之错 2009-7-14 03:32
- 新京报:龚建平 罪与罚 2009-7-13 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