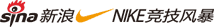《足球》刘晓新:中国足球该走哪条路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锁定四支直接出线名额,日本、韩国、朝鲜,再加上政策划拨给东亚区的澳大利亚,东亚球队空前地实现了一次“大包揽”。按照惯例,我们必须得先仰天长叹一番,然后坐下来以邻为镜开一个学习研讨会。这并没有错,毕竟东亚球队的压倒性优势,给中国足球的萎靡困顿制造了太过强烈的反差。即使是关于中国足球的话题早已是老调重弹,令人生厌,可只要它还没有麻木到毫无知觉,总还是应该拿出来说道说道。这个道理,就如同你家孩子长期学习成绩不好,你都认命了,可碰到邻居家孩子考了个第一名,你总还是忍不住会把自家那个不成气的东西叫到面前教训一番的。
更何况,这一次我们既不想沉痛地大批判,也不想聊胜于无地走过场。与我们国土接壤的三个东亚国家足球发展的道路,至少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一是日本所代表的全盘欧洲化的职业模式,二是朝鲜所代表的享受政策倾斜的计划体制。可摆在中国足球面前的现实话题,不是该学哪一种模式的问题,而是必须意识到,这恰恰是中国足球绝不可能走通的两条路。的确,很多事情,首先要想的不是该怎么做,而是要先搞清楚哪些不能做,做不得。这么一个看似细小的道理,说得玄乎些,却是中国足球长期悬而未决的路线问题和思想痼疾。
在中国,这是个大问题。
职业化,中国足球“国退民进”的灾难
日本足球十几年来突飞猛进,其足球哲学从根本上说并不复杂,他们始终如一在模式上模仿欧洲,在技术上追随巴西,就像这个偏执的民族,简单而认死理。而中国足球近20年来在风格上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非只是表面的摇摆,真正的死胡同却是,我们同样以欧洲为准绳,却只能识其皮而不知其髓。换句话说,我们一直认为自己职业联赛的反复是方式方法上的缺陷,殊不知,那些组织架构、市场推广上的舶来品,一搬到自己家里就破绽百出。
当初参与构建了职业联赛的李传琪,若干年后才有所顿悟:“当年我们无比激动,无比自豪,我们都认为是在为未来中国体育全面职业化走出第一步棋。”应该说,这就是职业化初期整个足球界的共识,那种解套之后的冲动与庄严的使命感,充斥了中国足球的每一个角落。可事实证明,至少在2008年以前,中国体育所追求的从来就不是什么职业化,市场化,也从来不需要谁或者哪个项目来下出这第一步棋。而足球的复杂性,高投入低产出,恰恰使其有理由被放置在整个计划体制之外,成为一项“样板工程”,在体育全球职业化的大潮下,证明中国体育也“可以有”、“真的有”职业体育。一项无关成败、无关痛痒的“样板工程”,被高调地理解为“重点工程”、“攻关项目”,中国足球对自身的错误定位,并不仅仅被定格为一时的历史误会,而是留下了一段漫长的尴尬历程。
其后的十数年时间里,中国足球考察必去欧洲,讨论必提英超,在“中国制造”风靡全球的年代里,难道一件职业化的马甲我们都造不出穿不像?也许,只有当年激情如郎效农、李传琪者,才能在多年以后看破风云一笑置之,这一群曾经以为自己在苦苦求索的人,分明就像是几乎被人忘却的《埋伏》中的冯巩。
抛开时间成本不计,这条弯路给中国足球带来的真正恶果是什么?我们不妨从最直接的层面去理解这个庞大的话题。大约在1996年到1999年的三年间,职业联赛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的“国退民进”运动,除了辽宁与广东两地,几乎所有省市职业俱乐部都干净利落地斩断了与地方体育局、足协之间的从属关系,就像冲破牢笼,奔向自由。职业市场与政府机构的平行,或许是职业体育的一大显著特征,但在国家职能至上的中国社会里,形而上的市场化早已被证明是无源之水。足球俱乐部与体育管理部门的“绝交”,迅速把自己放置在并不牢固稳定的投机性的资本链条上,而放弃了相当稳定的存在于计划体育体制当中的那笔资金。当时以为自己富得流油并且钱程似锦的俱乐部,生怕背后的婆婆分走一杯羹,却没有想到,把那些原来依附于全运会,依附于学校体系的青训系统,托付给本来就缺乏耐心的、一味追求品牌效应或政策补贴的资本,无异于为了站得更高,而砍掉了自己的两条腿。
再比如,一直到2005年,以“G7”为代表的俱乐部还在高喊所谓的“职业联盟”,可是狂热的人们追求了十几年,却没有来得及审视一下,“英超联盟”是不是可以飘移到中国来成为“中超联盟”?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在经济领域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全国工商联、青年商会或者企业家协会,该是什么样的组织?
据说,两年前的一次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上,万科的王石颇有感触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在中国应该怎么做企业。”他的欲言又止代表了无数人曾经的思考,中国足球15年的职业化改革,从时间上涵盖于中国经济改革的30年,和中国体育24年奥运战略的段落内,却既不符合整个行业的战略方向,也游离于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局部的成就太容易让人产生盲目的冲动,在某种程度上,职业联赛急转直下的这十年,就像是当年健力宝的李经纬、科龙的顾雏军或长虹的倪润峰,对政策的误读,往往就是玩火的开始。
朝鲜模式:一道博士生答不出的小学试题
我坚持认为,崔大林对足球界提及的“学习朝鲜”的口号,其实就是在表达一种“女排精神”,朝鲜足球顽强拼搏、国家荣誉至上的精神,使它有理由成为中国足球在本项目之中的精神榜样。但身为体育局副局长的崔大林,绝对无意于在体制上提出一个效仿对象,因为深谙体制优势的他,应该比绝大多数人都更明白,为什么中国足球学不了朝鲜。
客观上说,朝鲜体育与中国同属于计划体制、举国模式。但朝鲜体育追求的是点上的突破,对足球、篮球、拳击等自身优势项目,给予足够的政策倾斜和国家扶持。而中国体育追求的是面上的超越,从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的20多年时间里,以磅礴的气势、举国的能量打造出了一个体育超级大国。奥运战略,从本质上说,就是以奥运金牌为目标,从无到有,化优势为胜势。
没有人疯狂到认为,如果动用举国体制,中国足球也能拿世界冠军,但我们的确可以想象,如果仅仅以亚洲区出线为目标,以举国之力,强化外交,强调科研,重视选材,更重要的是把足球指标与各级体育主管部门领导的乌纱帽挂钩,大概还算是现实的想象。可是,出线,显然就与整个中国体育战略方针的核心目标相左。足球的重要性是全球性话题,而足球“让他们自己玩玩”却是中国式的话题。所以,我们面前的问题绝不是中国足球该不该学习朝鲜,而是根本无从学起。就举国体育的能量和成就而言,中国与朝鲜是博士生与小学生的对比,而上不了台面,入不了规划的中国足球,显然是一道博士生答不出来的小学试题。
遗憾的是,让中国足球明白这个道理却并不容易。即使是中国足协的头头脑脑、一大堆的中层干部,大多出身于本项目,一方面深信中国体育能制造那么多奥运冠军,不信搞不好足球;另一方面,又长期致力于以足球的社会影响力来说服领导,以求获得政策。可是中国体育水太深,不缺足球这条鱼,中国体育这盘菜太丰盛,不缺足球这道小菜。毫不夸张地说,也许耗费了十几年时间,足球界才明白,他们视若根基的职业联赛,其实在中国体育的游戏规则中,其标准无非是:既然求不了成绩,也就求个安全。联赛可以搞,但不要带来社会不安定因素,否则就南北分区,还不行就赛会制,再不济就索性不搞。
中国足球与朝鲜足球之别,并不在于体制之别,而在于地位之别。
南时代:头破血流后的无奈领悟
中国经济改革30年,无论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是围绕国家资源一体化的调整过程。宏观调控,从来为西方经济理论所不容,但在几乎无人幸免的金融风暴面前,就算是反对者,也不得不惊叹于“左右手经济”的神奇魔力。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同样用了漫长的时间,才解开了这道密码,摸到了自己头上的天花板。举国体育同样为职业体育所诟病,但中国体育的伟大成就,却越来越让这个行业的人们惊叹于它的威力。某种程度上,中国足球恰恰相似于在国有化经济大框框下的民营企业家,“中国国情”早已是一个老掉牙的词汇,有无数头破血流的经历之后,才可能有真正的领悟。
很多人认为,阎世铎和谢亚龙耽误了中国足球整整八年,可事实上,他们的目标单纯、目光坚定,不过是进一步践踏足球规律,极端放大片面需求的结果。与他们相比,南勇更愿意成为“搞足球”的人,也更愿意去把握在中国搞足球的“分寸感”,就像他上任之初所说的那样:“中国足球应该多想想,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如果让中国足球比现在好一些,南勇也许合适,如果说谁能挽救中国足球,那南勇一定不合适,因为没有人合适,因为在中国体育的政策环境下,中国足球其实不存在挽不挽救的问题。
中国足球究竟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上任数月,南勇几乎一言不发地在走自己看得见的路,比如奔走于亚足联与国际足联,修复中国足球的外交工作;比如以四线一体化的思路重新打造国字号球队;比如把青训工作重新托付给全运体系;比如与教委联办学校联赛……这是属于南勇的思路,也可能是中国足球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整体思路。
这是不是一条正确的路,取决于每个人的标准与期望值。可以肯定的是,王俊生“左”过,阎世铎、谢亚龙“右”过,南勇只能走在中间。中国人从来都很鄙视中庸,却最终都会走到中庸的一条路上去。
你可以认为,中国足球历尽沧桑,正在步入一个“左右手足球”的时代。
新浪体育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网友评论
相关专题:国足热身赛专题
更多关于 中国足球 的新闻
- 无痕:中超12轮5方面尽显中国足球暗淡的现状 2009-6-21 09:32
- 齐鲁晚报:中国足球该向朝鲜学什么 2009-6-20 10:01
- 长江日报:中国足球 一地鸡毛 2009-6-19 14:44
- 华商晨报:中国足球 此刻你的脸发烫吗? 2009-6-19 14:02
- 鲁中晨报:中国足球学不学朝鲜? 2009-6-19 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