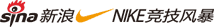东方体育日报:我的青春 我的大学
200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是“五四青年节”诞生5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这一天,3000多名北京高校的学生走上街头,以热血青春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帷幕。
无论是最初的群众基础,还是思想内核,“五四”都和大学无法分割。而无论在哪个时代,大学几乎都处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是新思想最热烈的萌发地和最深入的讨论区,所以,我们选择用54个曾经或现任的大学生的叙述,来呈现给大家一个我们眼中的“五四”。
“五四”是一条河,不同时代的青年以不同的体验和思考为它注入全新的内涵,才能保证它因鲜活而永葆青春,因而多元而奔流不歇。
我们为您记录一颗颗水滴,如果有幸,也许会有光折射到您的心中。青春作证。
何振梁 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1946-1950)
革命之路从大学开始
1946年夏天,我从高中毕业。停学还是去学生意?这是当时经济拮据的家里为我考虑了再三的问题。当时我恰好得到了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大学的部分奖学金,于是家里决定尽量克服困难,让我继续读大学。
在大学里我选读了电机系,学了这个专业,毕业后可以在法租界的发电厂工作,生活将有保障。震旦大学的课程全部用法语教授,这对中学时代在中法学堂一路走上来的我来说并不困难,在入学最初两年,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因为要保证功课好才能得到助学金继续上学。为了省钱,我经常只买最必要的讲义,有时甚至讲义买不起,只能靠上课全力记笔记或借同学的讲义和课本来抄录。即使如此,家里仍要时常变卖东西来支持我的大学开销。
1948年下半年,随着大形势的不断变化,地下党的力量在我校也发展得很快,我与一些进步同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在他们的带动下,我读了《交大生活》、《学生报》、《革命人生观》等进步书籍,我逐渐懂得要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希望。于是1949年3月,我参加了学校的地下学联小组。当时在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下,携带进步书刊很危险,搞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那时年轻气盛的我却以此为荣。同年4月,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上海人民保安队,组织宣传学习。我当时参加这些活动都已抱定随时牺牲的思想准备,并且后来我知道确实有许多进步大学生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沈煜 退休休干部 安徽学院土木工程专业(1944-1948)
一张迟到四年的毕业证
我读完了大学,各门功课都合格,但没有毕业文凭,只拿到一张证明,而且还是迟到的。1948年,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但我们的毕业文凭当时还是被送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盖章。结果,这些文凭在国民党逃去台湾时被一并带去了。我是安徽学院的第一届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当时我们很多同学都反映了这个问题,虽然并没太影响找工作,但文凭没有了总是不行的。后来到了1952年,当时我已经回到故乡杭州工作,有人补寄了一张毕业证明过来。因为文凭不能发两趟,所以那张纸就是证明了。寄信单位是安徽大学,因为那个时候安徽学院已经并入了安徽大学。
汪统 退休会计 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38-1942)
“转场”上课 战火中的大四
圣约翰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那个时候我们考大学没有现在那么复杂。我们学校有附属的高中和初中,我只有在小学毕业的时候考过一次,就升入了圣约翰大学的附属初中,然后就一路升到了大学。
读大学的时候,我的生活比较简单,把读书放在了第一位。上课的时候,做笔记很重要,因为老师一般都不会照着课本讲课;下课之后,也常常去图书馆找参考资料。
业余时间,我是体育运动的爱好者。那个时侯,有很多运动都是留学生带到我们学校的,比如田径、足球、网球、篮球和棒球,我们学校都是很早就开展了这些运动。同时,书法字画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爱好。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被苏州河隔开,我们读书还需要摆渡。大四秋季开学的时候,日军进攻租界,学校里没办法上课了,我们就只有到一个叫大陆商场的地方上课,早上我们去学校上课,下午就在圣玛利亚女校上课,桌椅都是借来的,每天走读。动荡的大四过去后,我就毕业了。教授介绍我到上海毛绒厂做会计。我们那个时侯毕业,工作虽然不包分配,但是很多学生的工作都是由教授介绍的。
赵兴田 退休干部 高级农艺师 安徽农业大学(1956-1960)
三班倒大炼钢铁
那个年代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运动。刚上大学没多久赶上“反右”斗争。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姑姑也是国民党的高官。所以,当他从农村实习回来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还有一些同学,他们因为响应号召提意见,所以也被打成了“右派”。到了1958年,“大跃进”又开始了,合肥的每个单位,包括大学和中学都轰轰烈烈地投入到大炼钢铁当中,我们学校也不例外。记得那时候是三班倒,我和我的室友总是被分在夜班。具体都记不清了,但就是记住了“累”,所有人都疲惫不堪,经常是刚刚睡着就被叫醒去接班。
刘平 退休职员 南京外国语学院(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1978-1982)
求学改变人生路
我那一届正好是恢复高考第一年,我是作为应届生参加高考的。我高考的成绩其实是可以留在上海读大学的,不过当时心里更多的念头是响应国家号召,报效祖国。再加上入学南京外国语学院就等于是光荣参军了,考虑到这一系列因素,我就去了南京。
大学阶段,所有的管理都是军事化的,要求相当严格。毕业的时候也是由学校统一分配,当时个人的理想都是以国家的理想为前提的。
毕业后,我在上海铁道学院(现同济大学沪西校区)外事办公室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出国热潮正好到来,我也渴望多学一点东西。工作的特殊性,也让我申请出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八十年代末,凭借着一点日语基础,我去日本语言学校就读,后来,因为机缘巧合,申请到美国的Dana大学学习经济专业。这么多年的求学之路走过来,从最初的一切服从国家,到后来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来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就是最大的不同吧。
管容 私营业主 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纺织专业(1978-1982)
密码写就恋爱纸条
在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一两年里,大学里都是拼命读书的学生,气氛挺严肃的。学校规定不准同学间“处朋友”,所以发展出校园感情的不多,就算有也没人敢公开。我在课桌上曾捡到过一张小纸条,上头全是点点划划,一开始还没弄明白,后来才想到,这不就是摩斯密码嘛。那时好奇心大,翻译了一句,结果是情人间思慕的话。没名没姓没落款,应该是某对“地下恋人”不小心落下的。后来,我帮他们消灭了“罪证”。我没在大学里交过女朋友,但等我快毕业那会儿,在校园里相互递信的同学已经多起来了,密码纸条用不上了。
许寄昌 退休工程师 上海交通大学金相与热处理专业(1960-1964)
碰上三年自然灾害 连体育活动都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