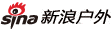体育 > 户外频道 > 空域-水域 > 知名登山者严冬冬遇难 > 正文
冲浪作家谈海南冲浪资源 遗憾海区消失
 山姆·贝利克利在海南体验冲浪,调查冲浪资源。
山姆·贝利克利在海南体验冲浪,调查冲浪资源。 山姆·贝利克利正在冲浪。
山姆·贝利克利正在冲浪。标题:冲浪板上的佛
英文:Surfing Brilliant Corners
文图/山姆·贝利克利(Sam Bleakley)
译/严冬冬 青铜雨
导语:山姆·贝利克利是全球最为知名的职业冲浪选手与冲浪作家,曾经先后在欧美获得过多次冲浪比赛的冠军头衔,并且一直为多家杂志撰写冲浪文章。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山姆先后游历了超过50个国家进行冲浪活动,这其中当然有也少不了中国。2004年,他第一次带领数名世界顶级冲浪高手进行环球冲浪活动,并且专门前往中国海南进行了冲浪旅行,随后他专门为本次环球冲浪旅行出版了专门的旅行文集《完美冲浪之地》(Surfing Brilliant Corners)。
正文
“把握眼前”是我在旅途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策划一次旅行,意味着随时都要考虑未来,尤其是以冲浪为主体的旅行,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来预判最好的浪将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天渐渐黑下来,我们需要找个地方过夜。我们开着车穿过杂草丛生的沙地回到公路上。这里周围群山环绕,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得一路开回海口才能找到提供食宿的地方。
路上,我们超过了不少骑自行车和三轮车的人,还拍摄了人们在忙碌的照片。我看见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正在打牌,他的脸并不粗砺,而是像丝绸一般柔软,目光不是投在面前的对手身上,而是彬彬有礼地打量着地面。不需要视线的接触,只要一个眼神、一个姿态、一个手势就足够达到交流的目的。中国人交流的方式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偏重间接复杂的暗示。我们在竹屋门前停了下来。打牌的人们啜饮着米酒,并没有抬头,似乎根本没注意到我们。不过,他们当然已经清楚了我们的来意,只消侧目一瞥就足以表达这一点。
我们探索了一片覆盖着雨林的海滩,所凭的资料只有一份海图和一张勉强能看懂的中文地图。公路逐渐变成了土路,几辆摩托车溅着泥水经过,路边传来咯咯的鸡叫还有成群的短尾猴从树上掠过。我们在靠近岸边的波浪中玩耍了一阵,又坐在渔人的屋檐下纳凉。不过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在佛像目光下度过的时光,那种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在眼前一刻的感觉,就像奥奈特·柯尔曼(Ornette Coleman)融合了中国、马来、印度传统风格与摇滚旋律的乐曲。
我很快学会了几个最基本的中文词汇——“你好”、“谢谢”和“再见”。我们试图跟更多的本地人交流。他们讲话声音很大,抽着烟,随地吐着痰,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表面看上去跟那些安安静静打牌的人完全不算是同类。但我也开始欣赏他们那种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眼前一刻的专注。他们很镇静,很有信心,几乎不会为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而眨眼。或许表现出惊讶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吧。
风逐渐停了,浪也安静下来,我们包了一辆车,打算去岛的北部看看。司机每次穿过村庄的时候都要按响喇叭,从路边的骑车人旁侧驶过。我们缓慢地穿过省会城市海口,这里充斥着炎热和潮气,街上车辆来往如织,叫卖声此起彼伏。这是一座简单但却并不简陋的城市,我看见有人正在用白瓷砖装饰新房的外墙。在中国,三股截然不同的力量正在汇聚到一起:西化的潮流——衣着,快餐,朋克音乐和日本制造的摩托车——以及传统的力量(或者说对传统的重新诠释),还有国家社会主义仍旧强大的控制力。“展望未来”已经取代了“回首过去”。中国正在从历史走向未来,文化环境日新月异。然而快速的工业化,以及都市风格的国际化,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北京上空笼罩的烟尘堪比十九世纪的伦敦。
全球化的潮流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当时的欧洲商人们正在寻找通往中国的更短航路,目的是为了用白银换购便宜的黄金。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大陆掠夺了大量的白银,欧洲市场上白银对黄金的兑换价已经达到12:1,而在中国的兑换价则只有6:1。导致世界市场变得如此开放的,正是来自中国的三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和火药。指南针让远洋航海成为可能,纸张方便了交易的进行和账目的记录,而火药和火器则让欧洲人得以征服北美五大湖区的土著,开辟从大西洋到哈德森湾的商路。这条商路原本的目的是为了缩短与中国交易的距离。传说中东亚地区的巨大财富让欧洲各国都渴望分一杯羹,这正是十七世纪欧洲第一波全球殖民浪潮的推动力。
 不幸的是,由于码头的建设,最大的一片适宜冲浪的海区很快就要消失了。
不幸的是,由于码头的建设,最大的一片适宜冲浪的海区很快就要消失了。走在海南岛最北端空旷的沙滩上,我又一次感觉到了历史的厚重,尽管这历史已经为近来的纷争和变革所掩藏。这里并不适合冲浪,因为琼州海峡的大陆架很浅,波浪的能量刚聚积起来就被消磨掉了。岸边是一排排废弃的碉堡,一直延伸到水里。从明朝的万里长城——尽管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却未能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到毛泽东主导的“上山下乡”,孤立主义一直是中国历史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我们返回海岛南部的时候,附近的学校刚好放学,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回家,车后面拖着菜园里用的竹耙。绝大多数孩子都似乎没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最多只是眼角的一瞥,仿佛他们尽管对我们很感兴趣,但却觉得直视过来不太礼貌。
浪并不大,我最终说服几个孩子尝试一下冲浪的感觉。在别的地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孩子们很快就会争夺起冲浪板的使用权。但在海南,孩子们天生就具有足够的耐心。他们轮流尝试,很快都掌握了基本的技巧。中国人一直都具有优秀的运动天赋。因为懂得阴阳调和的道理,所以他们的平衡感相当出色。即使在国家社会主义达到巅峰的日子里,中国的两大彼此对立的传统,儒家和道家思想,也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礼制与服从,而道家思想的核心则是独处和顺从自然规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里,儒家和道家的精神内涵已经深入了中国人的骨髓。孔子认为平静的水面能够反映出最完美的平衡,人们在社会中应该追求“心如止水”的状态。道家则认为自然犹如一场风暴,而你则处于风暴最中央的宁静区域,既身处其中又游离于其外。而在冲浪中,则有浪管和浪峰之间的对立统一:驾驭这两者都需要完美的姿势,动态的平衡,以及身处风暴之眼所需要的镇静。
孩子们使用的是我新买的T&C牌环氧树脂冲浪板,上面的商标正是道家的阴阳图形。这款长型冲浪板的设计发源于夏威夷,生产则是在亚洲的现代化工厂,完全采用自动化的批量制造工艺。这一类轻量而坚韧的冲浪板是在最近二十年里逐渐发展出来的,非常适合长途旅行。当我跟这些孩子们一样大的时候,对阴阳的了解仅限于T&C品牌商标——这就是广告营销的影响力。T&C的产品测试员都是历史上最自由、最前卫的冲浪者——70年代的“橡皮人”莱瑞·波特曼(Larry "Rubberman" Bertlemann)和戴恩·基洛哈(Dane Kealoha)(两人都在盖瑞·洛佩兹[Gerry Lopez]开创的夏威夷式平滑风格基础上更上层楼),80年代的马丁·波特(Martin Potter)。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在复杂狂野的移动过程中保持平衡的能力。
精力充沛、不拘小节的波特曼,在70年代中期的加州开创了“像玩滑板一样冲浪”的风格,因为这种风格最初是在威尼斯海滩的荒僻地带发展出来的,所以被称为“狗城(Dogtown)式冲浪”。近十年后,佛罗里达州的滑板高手罗德尼·穆伦(Rodney Mullen)完善了从平地凌空腾跃的“豚跳”技术,加州的冲浪者们立即把这种技术运用到了冲浪当中。在英国出生的波特跟加州本地选手克里斯汀·弗莱彻(Christian Fletcher)和马特·阿基波德(Matt Archibold)一样,都很擅长腾跃动作。波特凭借强大的力量、灵活的切转和出人意料的凌空翻滚而出名。他的照片登上了1984年的《冲浪》(Surfing)杂志封面,跟汤姆·卡伦(Tom Curren)、汤姆·凯罗尔(Tom Carroll)和马克·奥奇卢波(Mark Occhilupo)一样,都是90年代“惯性一代”冲浪者成长过程中的偶像。由泰勒·斯蒂尔(Taylor Steele)拍摄的“惯性”(Momentum)系列视频,以美国顶尖冲浪者凯利·斯莱特(Kelly Slater)、罗柏·马卡多(Rob Machado)和夏恩·多利安(Shane Dorian)等人为主角,他们的精彩表演一时间掩盖了之前那些优秀冲浪者们的光芒。之所以在这里追忆冲浪运动的历史,是因为传统风格的长型冲浪板在今天的年轻人中间重新流行,可以看作是对强调直截了当的“惯性风潮”的逆转。而在中国,我发现这里的人们彼此交流的方式,无论是面对面的交流还是孩子们对冲浪的初次尝试,都正好是“直截了当”的反面。那是间接的、似乎不经意的眼角一瞥,不是全神贯注的盯视。我们把这种气质理解为“礼貌”,但它并不只是这么简单。它是一种优雅而复杂的交流方式,尽管并不直接,但却十分有效。
澳大利亚的天才冲浪者彼得·卓音(Peter Drouyn)在70年代初就探索过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带。尽管他宣称这里的冲浪资源十分优秀,但却没有带上摄影师,没有拍回精彩的照片,所以当阿尔比·法赞(Alby Falzon)发布巴厘岛周边的冲浪报告时,他的探索结果很快就被忘却了。卓音于1985年重返中国,在海南找到了不少适合冲浪的场所。以他一贯的高调,他向中国政府建议组建一支国家冲浪队,由他出任教练。他相信冲浪很快就会成为奥运项目,而中国的冲浪者将具备夺冠的实力。但是或许由于他太过张扬,中国政府不仅对这项建议置若罔闻,而且拒绝延长他的签证时间。卓音只能两手空空回到澳大利亚。
直到今天,商业化的冲浪运动还没有进入中国。但是中国拥有全球近六分之一的人口,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以上海及周边经济区为例,这是一块庞大的地区,面积是加州的两倍,沿长江三角洲平铺开来,就像是一条由水泥和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巨龙。旁边就是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具有丰富的冲浪资源。或许道家思想可以成为冲浪运动在中国扎根的依据——城乡之间对立统一的完美平衡。
那天夜里月亮很圆,还可以看到锈红色的火星。尽管我对中国人的了解还相当片面,但已经开始从中总结出他们的共通气质。我们驾车来到海岛最南端的三亚市,这里过去曾是一个安静的渔村,如今则成了热门的旅游区。我们穿过大街小巷驶往旧码头区,码头上随处可见衣着暴露的夜店女郎和光顾她们的男客。海滩就在附近,但是条件并不理想,小贩们争着向我们兜售纪念品,回族妇女们则叫卖着珍珠项链和槟榔。沙地上到处是嚼槟榔的人们留下的红色唾痕,我们看见的许多人牙齿和嘴唇都染成了棕红色。
在习惯了东海岸的宁静之后,三亚这种“罪恶都市”一般的喧闹让我们惊讶不已。金黄色的沙滩成了游客们的乐园,这又是国家社会主义与经济效益结合的明证。三亚被称为“东方的夏威夷”,但是从冰冷的北国飞往这里的中国游客们似乎并不习惯海滩上的生活。我们发现
 这里具有全海南最棒的冲浪条件——理想的水深加上形态各异的礁石,如果有台风造成的浪涌。
这里具有全海南最棒的冲浪条件——理想的水深加上形态各异的礁石,如果有台风造成的浪涌。,一定颇具乐趣。不幸的是,由于码头的建设,最大的一片适宜冲浪的海区很快就要消失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允许个人获取土地的使用权,所以不少地方的海滩都成了私人地盘。
在南山文化旅游区,我们花钱买了门票去看海,在被海浪打磨光滑的花岗岩柱间转了转,这就算是所谓的“大自然体验”了。我们在这里只待了几天,花销却比在东海岸的两个星期要大得多。到处都有导游带领着成群结队的游客,穿着鲜艳的休闲服装,戴着遮阳帽。离开旅游区需要先穿过一片商铺,糖果店、化妆品专柜、服装店和纪念品店全都开在一起。真是古怪的一幕!我还记得在我的故乡,不列颠最西端的海角(“下一站就是纽约!”)被建设成了“天涯海角游乐园”招徕游客,现在想来,那里跟南山或者科尼岛的游乐场也没有什么区别。今天的许多文化评论家都认为,全球化历程就像是游乐场的建设,到处都少不了某些共同元素——麦当劳,可口可乐和耐克。那些十七世纪的探险家们如果知道今天的中国正在变得跟他们的家乡别无二致,又会作何感想?
我很希望能再度拜访中国,欣赏内地的美景和绚烂的艺术,进一步了解那里的人们和文化。但是这一次的旅程让我心中百感交集。我去过的很多地方并没有太好的冲浪条件,但是当地文化给我带来了丰富的体验。而在离开海南的路上,我回忆起佛像目光下的宁静安详,以及海滩上喧闹拥挤的小贩,回忆起乡间人们眼角的一瞥和宾馆里的敲诈勒索,心中五味杂陈。我怀念着那种流畅的、变化的、充满新鲜内容的感觉。
爵士乐大师们发自心灵深处的演奏,有时能像子弹一样击中你的心脏。如果乐曲像大锤一样击打你的头脑,就说明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你只会被弄得头昏脑胀,失去敏锐的感觉。而你需要的是真正像子弹一样致命的乐曲,让你在被杀死之后又得到重生。有些下三滥的爵士乐手只知道制造噪音,但是谁又需要更多的噪音呢?像约翰·科特兰(John Coltrane)和大卫·穆瑞(David Murray)这样的即兴演奏天才,总能吹奏出华丽而又激烈的旋律,把变化推进到极致,将乐符间所有可能的组合都尝试一遍,直至穷尽所有的变化内容为止。当莱瑞·波特曼最初出道时,人们把他称作“橡皮人”,因为他总能做出匪夷所思的动作——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转弯,朝不可能的方向移动,利用全部可以利用的能量积聚速度,从原本不可能通过的地方疾冲出来。波特曼可以紧咬波浪的尾迹,让一切突然间颠倒过来,再开足马力向前冲刺,追逐爵士乐一般的自由。他的冲浪风格正如同科特兰的音乐风格一样。他的独奏永无止境,因为前方的道路永无止境。偶尔也会有天才的冲浪者能够把科特兰式的激烈和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式的开放结合在一起——像是凯利·斯莱特、莱尔德·汉密尔顿(Laird Hamilton)和乔尔·都铎(Joel Tudor)这样的顶尖高手。之所以戴维斯会邀请科特兰担任乐队里的萨克斯手,当然是有原因的。太过激烈会让人难以应对,太过空旷则会让人无以仰赖。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伟大的乐队和伟大的冲浪者。
关注新浪户外(微博),了解更多户外资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