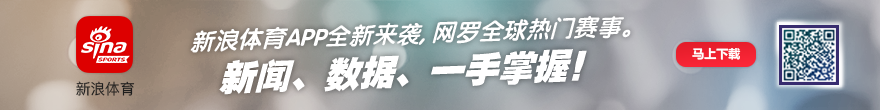二人二骑,行向蒙古国最西端。本文摄影均为 Jamie Maddison 图
二人二骑,行向蒙古国最西端。本文摄影均为 Jamie Maddison 图
[编者按]旅行摄影师杰米·麦迪逊在这篇文章中记叙了自己和朋友骑马横穿蒙古西部边陲大草原的难忘经历。在这次旅程中,他们不仅学会了草原骑马的技巧,懂得如何照料马匹、与牧民们和谐相处,同时也幸运的找到巴彦乌列盖省传奇的鹰猎者,目睹了拥有千年传统的“金鹰”捕猎全过程。
岩石、沙砾和天空模糊成一团,从我身边飞速流走。世界在我的马儿脚下铺开,铺得又平又远,铺向包围我俩的空旷草原。
风野蛮地掠过卡夫卡的鬃毛,穿过我因凛冽的蒙古空气而冻僵的双手之间。我努力控制这疾速奔跑的动物,它因要回到宿营地而无端兴奋起来。忽然间,一股深深的恐惧感袭来,我眼睁睁地看着马儿在石头上绊了一下。我被甩得前俯后仰,而马儿后腿直立,仿佛要弥补自己的失误。一眨眼,我的脚就脱离了马镫,朝光秃秃的地面上栽去,然后在厚厚的沙土中翻滚到眩晕。好在堕马的角度救了我,我还能站起身来,来得及目睹马儿奔向远方。它成了一个孤独移动的斑点,奔向平静而空旷的土地。
“这匹马归你了,杰米,”阿帕梅斯对我说。一条被阳光晒得褪色的、扭成麻花的马缰绳塞到我渴望的双手中,“这匹归你,马特……它们没有名字。”
在暴烈的蒙古阳光下,我欣赏着这些美丽的动物:心血来潮间,我决定给我的马儿起名叫做卡夫卡,而我的伙伴马特(马修·特拉弗)则给他的马取名拉里。于是阿帕梅斯——他是我一位熟人的哈萨克族朋友,也算是我们这次旅程的向导,他开始在辛劳的驮畜身上载满补给,这些储备将支撑我们走过前方的200英里旅途,穿过蒙古国最西端的巴彦乌列盖省。
 草原里的蒙古包
草原里的蒙古包马特和我来到这里,当面见到了阿帕梅斯,想要跟他一同骑马,希望向他学习在草原上照料马匹的技巧。明年,我们三人将一同骑行1700公里,一切都是为了这次冒险做准备。此外,我们还来寻找巴彦乌列盖省传奇的鹰猎者,给他们拍照、与他们共骑。
鹰猎已有千年传统,鹰猎者们依靠自己亲手喂养大的巨型“金鹰”捕猎为生。抵达边陲小镇乌列盖绝非易事。短短三天中,车胎扎破了三次,还有一次几近灾难:一辆汽车从小山丘上飞速冲下来。相比之下,骑马显得温和多了。
“好啦,好啦!出发吧!”阿帕梅斯吼道,他那蒙古人的身影紧紧包裹在帽子、围巾和风衣里,保护他不被中亚即将到来的寒冬冻伤。薄雾蒙蒙,天空湛蓝,景色向我们四面八方铺展开来。我多年没有骑过马了。马特则从没在马背上呆过,——也可能很久之前,他还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海边遛过小马吧。然而,我们倒还知道要买些合适的骑马装备:马裤、蒙古马靴,最奇怪的要数一袋苹果味的马零食。
幸运的是,蒙古马不仅吃苦耐劳,而且体型较小、性情非常温和,很少受惊。地面上覆满了动物发白的尸骨。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哪怕受点小伤,后果也可能非常严重。“只要不从马背上掉下去,那就没事,”我天真地推断道。
 马背上驮着支撑我们走完200英里旅程的补给。
马背上驮着支撑我们走完200英里旅程的补给。我们骑马穿过草原。透过墨镜看出去,无云的天空是紫色的。马特用他的小型广角运动摄像机录下了许多场景,这个摄像机就一直架在他的手杖上,勉强算个三脚架吧。当天晚上,我们住在一顶温暖的游牧帐篷里,牧民倒了一杯又一杯盐分极重的茶。等我们觉得自己都要把死海喝干了,一个三十出头、始终微笑着的哈萨克人开始磨他的钝刀。
我正猜测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牵了一头咩咩叫的绵羊来到前门,供我等品鉴。我们把锋利的瑞士丛林军刀借给了哈萨克人。靠着多年经验凝成的技巧,他用刀迅速挑开它的喉咙,剥皮,不过一小时,就把绵羊料理干净。那天晚上,我们掳起袖子,共同享用了这一堆羊肉和内脏。随后,马特听着阿帕梅斯即兴弹起了两根弦的冬不拉。我透过帐篷唯一的天窗向外望去:黑夜渐渐袭来,世界陷入黑暗。
凛冽的风挤过山口飞驰而来,打在我们脸上。我弓身坐着,躲在新买的始祖鸟牌防风衣下面。这件夹克的面罩和风帽替我挡开了严寒,却也让我远离了外部世界。随着有节奏的马步,我在马背上前后摇晃,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卡夫卡倒是因陡峭的爬坡,浑身汗水闪亮。汗水汇成小溪,从它两胁处流下,混杂着尘土、在毛发的末端结成灰色的箭头。
 与鹰猎者们相遇
与鹰猎者们相遇随着海拔上升,附近的河流结冰了。白色的水道蜿蜒而下,朝阿尔泰山脉方向而去。到小镇还须骑行一天。好在我们的帐篷只要几分钟就搭了起来,内里空间宽敞,足够我们把所有行李收进来,以免被夜晚的低温冻坏。不过,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睡袋上还是因自己呼出结满了厚厚一层冰。下午时分,终于抵达小镇,我和马特都很高兴,而我想到终于要见到鹰猎者并与之共骑——在出发前的许多个月中,我读过多少关于他们的故事呀!
金鹰冲向天际,抛下它的主人和我。两人伶仃地站在冷而荒芜的山巅,空旷的草原从我们脚下朝四面八方延伸而去,直到遇见一片弧线平缓的雪山,阻挡了视线。我用我的高性能望远镜观察着鹰的飞行,它的双翼在白色的天穹上伸展。忽然,阿帕梅斯在山下吼了一声,山谷间回音震响:一只兔子正跑过碎石坡,而金鹰已然逼近,它无情地扑向自己的猎物,它的暗影在地面上浮动……我们每个人都透过望远镜紧张地注视着战况。正当鹰爪将要握紧时,那只勇敢的小兔子猛地冲向一边,闪电般钻进了兔子窝,永远地摆脱了那位沮丧不已的捕猎者。
鹰猎者们有些失望。山巅处,他们在马背上挺直身子,身穿华丽的传统服饰,头上戴着红狐皮帽子。他们像模特一般摆着姿势,各自在不同的山头,成为天际的风景。阿帕梅斯的父亲达莱可汗在三个人当中站得最高,他如王者般安静地看着儿子努力让他的猎鹰站在自己光溜溜的手臂上。显然,这鸟儿的爪子把我们的朋友抓得很痛,即使这么远我也能看出他扭曲的表情。
 阿帕梅斯的父亲达莱可汗,与他心爱的猎鹰
阿帕梅斯的父亲达莱可汗,与他心爱的猎鹰我们再也没看见任何猎物的踪迹,鹰猎者们显然很失望,但我却很开心。那些有翼死神从高空俯冲下来时携带的无情和恐惧,这里的动物们算是暂时幸免于难了。
马儿休息好了,活蹦乱跳,与鹰猎者的会面对我而言实在太过短暂,但我们必须回到草原上,继续骑行。我们三人已经在马背上度过了漫长的三天,但卡夫卡显然毫不介意。
“我大概不应该激发它这么充沛的精力,”我琢磨道,胆战心惊地碰碰我那早已肿起来的脚踝。而我的马儿,它刚刚把我不留情面地撂在地上,自己小步跑开了。
“你还好吗?”我听见马特在我身后说,他正骑着拉里。我还没能挤出一句应答,他就开心地问道:“摄像机在哪儿?它没事儿吧?”我把运动摄像机递给他,感觉自己蠢透了:机器的显示屏都花了,外壳也成了碎片。
“哦,真棒,摄像机没法倒带了,摔坏了,”他暴躁地嘟囔着,“等等……没准还没坏,老天,你就不能把它好好拴在自己身上吗?”
“你能不能先关心我一下?”我生气地反驳道。但阿帕梅斯遥远的身影吸引了我们,从而避免了一场争吵。他跳到没有马鞍的马背上,然后轻松地骑过我那段跌跌撞撞的路程,继续随意地在平原上奔跑着。
 牧民家的小孩笑靥如花
牧民家的小孩笑靥如花天气变脸太勤快,越来越糟。整整两天都寒冷刺骨,即使我裹着Brynje牌的基础层、细绒卫衣、AlpKit牌厚马甲、贝豪斯牌羽绒夹克,再加上始祖鸟防风衣……气温已低于零下12度,我坐在马背上无法活动,感觉自己像是在严冬季节里去斯科费尔峰顶度周末,一丝不挂地享受日光浴。接下来开始发烧。我们催着马儿穿过几条浮冰碰撞的深河,身体无比虚弱,恨不得从鞍子上滑下来——只要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我叫马特把我绑在鞍桥上——我是认真的。
那天晚上,我们不得不在一间挤满人的帐篷里过夜。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跌跌撞撞地挤出了帐篷,大口大口吞下午夜的凛冽空气。雪下得很大,但一丝风也没有。雪花温柔地落在我烧红的脸上,让我仿佛变成了古老的黑白圣诞电影中的人物。我听见我们的马在不远处发出窸窣声,马蹄把松软的白色雪地踩得咯吱作响,而此时一轮皓月忽然拨开云层,照亮我周身壮丽的风景,让我得以目睹奇境。
我如饥似渴,饮下美景如醇酒——这时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本次旅程所剩时日无几,于是我又一次明白我们是多么幸运,能够来到这片边陲之地。从我踉跄的脚步之下,草原铺开,无边无际。在我因发烧而兴奋的脑海中,这片草原似乎会无限延伸下去,到世界的尽头再回转。它容纳了我们经过的所有奇遇,却还藏着更多尚未经历的可能。在这里我们学到了许多草原骑马的技巧,而真正的考验几个月后才会到来,那时我们将踏上真正的骑行之旅。
 脚下无边无际的草原
脚下无边无际的草原关于作者:
杰米·麦迪逊是一位作家、摄影师,也是四处周游、雄心勃勃的冒险家。起先,他为英国攀岩杂志《攀岩者》工作,在新闻业的广阔天地中初试啼声。自此之后,冒险生活的诱惑就攫取了他。他多半时间都在筹划旅行,用文字和影像描写旅行中的方方面面。他曾为《国家地理杂志》和《不为人知的欧洲》等杂志撰稿,曾获《国家地理杂志》年度旅行摄影师奖提名奖。过去两年间,杰米一直在筹划一次跨越欧亚大草原的探险之旅,他的目标行程直指3万公里,其中有2千公里要独自在马背上度过。
(文章内容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