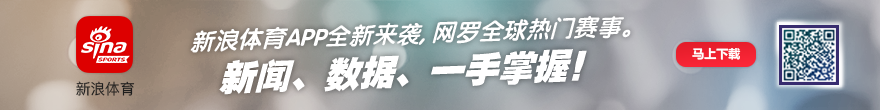贮贝器
贮贝器
滇国是我国西南边疆的古王国,以今滇池区域为中心,旁及周围数百里之地。战国末至西汉中期,为滇国的最繁荣时期,当时农业、冶金和畜牧业均较发达,马的数量很多,使用战马的历史也早,尤其很早就出现了马镫,比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马镫还早四百年。因此我国最早使用马镫的历史,应从西汉中期滇国的绳圈式马镫算起。
一、滇国的马及战马
滇国畜牧业发达,牛马等大牲畜数量很多。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武帝时司马相如、韩说初开益州郡(郡治滇池县,今云南晋宁县),“得牛马羊属三十万”。《汉书·西南夷传》也说:“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汉将田广明用兵益州(郡)获畜十余万”。又《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刘尚击益州郡少数民族头人栋蚕,得“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也正因为滇池区域畜牧业发达,牛马较多,所以中原王朝向云南少数民族摊派的贡赋,也是以牛马等大牲畜为主要项目。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蜀汉时诸葛亮平定南中,指令云南少数民族以“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西晋时李毅为南夷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每夷(部)供贡南夷府牛马动以万计……其贡郡县亦然”。云南少数民族每部贡南夷府的牛马以万计,还要照样给当地郡县官吏们一份,如果没有滇国时期发达的畜牧业,蜀汉和西晋时云南少数民族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牛马作贡品。中原王朝向云南少数民族索取贡品虽多多亦善,但能否完成规定数量还是心中有数的。《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当时滇池区域有“金银、畜产之富”,“居官者皆富及累世”,是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
滇池区域不仅产大量马匹,还有名盛一时的良马“滇池驹”。《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滇池县,郡治(益州郡所在地),故滇国也……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日滇池驹。日行五百里”。与神马交固属神话,但古代滇池区域产良马,体小而雄骏,尤善山行,这倒是真的。东汉安帝时令益州郡设“万岁苑”,专养战马,大概所说的就是“滇池驹”吧。
从滇国青铜器图像看,马的数量较多,其中有的用于出行骑乘,多数则出现在战争和狩猎场面中。战争和狩猎所用的马都是战马,要经过严格训练后方使用。因此滇国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马的调养和训练,青铜器上也有驯马场面的出现。如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1件贮贝器,盖上有驯马场面,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滇国训练战马的情况(图一)。此贮贝器盖上共雕铸十人和七匹马,盖的中央铺一块中间圆、两头方的条形铜片,想必原来是地毡之类的铺垫物,其上置一圆形座,座上端坐一椎髻男子,耳佩大环,手戴宽边玉镯,衣着华丽,一望便知是滇王属下的酋长或头人之类。中坐者身后有一人执伞,伞已脱落。身前有一人作半跪状,腰佩短剑,双手前伸,头微斜,嘴略张,似在向中坐者报告驯马情况。中坐的头人满脸怒气,一手后扬,一手前伸,用食指指向前跪者,大发脾气。其外有七个佩剑男子,服饰全同,每人手中各牵一马之缰绳,列队向同一方向走动。以上图像,显然是一个训练战马的场面,中坐者为头人,因训练战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必须亲临现场监督。前跪者为负责驯马的小头目,在向头人报告训练情况,也许头人并不满意,故满脸怒气,手指小头目大声训斥。周围的七个佩剑执缰绳的男子均属驯马的士兵,所驯之马为战马,训练合格后即用于战争和狩猎活动。
二、滇国的马具
从出土青铜器图像看,滇国马具经过了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三个发展阶段。
(一)仅有缰绳及坐垫阶段
战国晚期,滇国虽有战马及马具,但尚处于较原始状态。如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1件“骑士猎鹿”铜扣饰,二骑士各踞坐于马背,手持长矛作下刺状,马前有二鹿,其中一鹿已被刺倒地,一猎犬回首作惊惧状,其下有一蛇,口咬一马之尾部(图二)。此骑士所乘之马只有缰绳,因当时尚未出现络头和马衔,所以缰绳只能系在的马的口中,马背上无马鞍,仅有较长的坐垫。可见当时滇国的马具还不很完善,故骑士不能跃马急驰,在马背上的动作亦不甚自然。

(二)鞍辔齐备阶段
西汉中期,滇国的马具、马饰均臻完善。当时马头上不仅有额带、鼻带、颊带和咽带皆备的络头,也有泡丁、当卢等马饰,还出现有衔、镳、镝成组的马衔。按《说文·全部》:“衔,马口中勒也”。至今云南仍称马衔为“马勒子”。衔环中间的实心圆球称“镝”,《淮南子·泛论训)高注:“镝,衔中央铁,大如鸡子黄,所以制马也”。衔环两侧的条形铜片称镳,亦作

,因为此物古代亦有角制品。此类成组的马衔在江川李家山西汉中期墓中完整地发现过,衔环中间的镝也正好是铁制品(图三)。

此外,西汉中期滇国战马上还出现鞍垫、攀胸、后鞦、腹带齐备的马鞍,以及相应的带扣、策子等铜饰件。如晋宁石寨山贮贝器盖上的战争场面中,一骑士被击中坠地,马作逃遁状,由于是“逸马”,马背上的鞍具看得十分清楚(图四)。此马鞍为前高后低的“桥形鞍”,前桥高起并分作两关,便于手扶,使骑士在下坡时不易前倾,后桥较低呈斜坡状,方便上下。鞍前有攀胸,下有腹带,使马鞍紧贴于马背,不致在跑动时使鞍具松弛、脱落。从青铜器图像看,滇国战马上都有攀胸和腹带,有的也有后鞦,尽管马鞍被骑士的战裙覆盖,但仍可以肯定马背上是有鞍具的,否则攀胸、腹带、后鞦无处拴系,设之又有何用?

(三)马铠阶段
西汉中、晚期,滇国的马具更加完善,除原有的马鞍、络头及衔镳等继续使用外,又新出现了马的防护用具“面帘”和“当胸”。如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1件西汉晚期的刻纹铜片,其上刻一个骑马急驰的骑士,此人蓄尖顶形发髻,身披毡,酷似近代的彝族男子形象。所乘之马的面部有一“面帘”,似用皮革制成,遮住马的前额及嘴部,其上有两个圆孔,便于马的眼睛外露。另外此马的前胸亦有覆盖物,是用来保护马的胸部的(图五)。江川李家山墓地还发现1件铜制鎏金的“面帘”模型,整体作马面形,马的双眼及两个鼻孔处均有孔洞,显然是为便于观望和呼吸。可见当时滇国确有此类面帘实物的存在,不过不一定是铜制或鎏金的。
面帘、当胸虽属于马铠的组成部分,但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马铠。云南古代完整的马铠见于东晋太元年间(公元376—396年)昭通后海子壁画墓,为左、右两大片,似用整块的牛皮制成,中间用绳索穿系,置于马腹的两侧。不过那已经是滇国以后的事情,故不在此详述。

三、滇国的马镫
马镫是马具中较晚出现的一种特殊器物,对骑马作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马镫的国家,而我国马镫的最早发明和使用者,则是滇国古代的少数民族。
西汉中期,滇国战马上已普遍使用了马镫。不过当时的马镫并不是用金属制作,结构和后来的马镫也有区别,但其作用是相同的,都是为提高骑兵的作战能力,使骑士全身的力量更容易发挥出来,上身及双手也更加灵活自如。如晋宁石寨山西汉中期13号墓(该墓只出汉文帝四铢半两而未见武帝五铢钱,其时代或可早至文帝时)出土l件贮贝器上有战争场面(图六),此图像中央有一骑马急驰、手持长矛刺杀的主将,余皆为步卒,手中亦各持有兵器。骑马者戴盔着臂甲,腰佩短剑,身着战裙,此人通身鎏金,说明他的身份较高。所乘之马肌壮体肥,马饰、马具俱全,马颈下系一人头,当属猎来敌人之头颅。此马马鞍前沿两侧各系一绳,下垂至马腹,绳端另结一圆圈,骑士双脚的大拇指各伸进一圈,蹬向马腹前。类似的马镫,在滇国青铜器骑马图像上不止一处发现过,说明这种简易的绳圈式马镫,在当时云南少数民族中流行颇广。直至近代,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仍有用绳圈作马镫的,但绳圈较大,用整只脚踩踏,不像古代只用一个大拇指。也有的在绳圈下加一条木棒,用整只脚蹬在木棒上。一般都不使用金属蹬,少量金属马镫都是从内地买来的。
滇国青铜器上的马镫图像,是目前我国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和最原始的马镫。时代为公元前二世纪后半叶。用双脚的大拇指套在绳圈中作马镫,也是符合云南少数民族跣足的传统习俗。云南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多无穿鞋的习惯,包括妇女和一些身份、地位很高的人。正如樊绰《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说,南诏时“俗皆跣足,虽清平官、大军将不以为耻”。而绳圈式马镫,正是适应跣足民族骑马的特点产生的。
关于马镫,我国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最早是由中国发明的。就现有考古资料,我国最早的马镫发现于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年)的1件陶马上,这比滇国少数民族的马镫晚了近四个世纪。而且西晋时期的马镫只是在马鞍左侧靠近鞍桥处有一个三角形的蹬,据说为了能迅速上马蹬踏用的,上马以后就不用了。至于中原地区真正马镫的出现,那已经是五世纪初叶的事了。其实,马镫的真正作用并不是为了上马迅速,它可以使骑士和战马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和马的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骑士的双脚蹬在马镫上,上身被解脱,手中的兵器也更能发挥作用。滇国的马镫已具备了上述功能,比起西晋时期仅能起“上马桩”作用的单边蹬,自然要进步得多。至于用绳圈或金属制作,那只是材料问题,对马镫的进步于否,并不起决定作用。

四、滇国马具发达原因初探
滇国马饰、马具发达,使用马镫的时间也早,自然和云南多良马,当地民族骑马历史悠久有关。而云南很早使用战马,不用战车,这又和当地多山少平地的自然条件相关联。因此要搞清楚滇国马具发达及马镫出现早的原因,首先必须从云南悠久的骑马史和特殊的地理环境说起。
云南少数民族骑马历史久远,比我国内地早约五个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剑川县西湖青铜时代遗址中发现有马骨,经古动物学家鉴定为驯养马,但不知是否用于骑乘。公元前九世纪初,德钦县纳古石棺墓中发现一种直径五至7厘米的圆形饰片,背上有鼻钮,内插小木棍,可能是一种马饰。内蒙古“匈奴墓”中有类似的装饰品,也是以马饰定名的。另外德钦县永芝石棺墓中还发现过铜泡丁,是马络头上的装饰品。马饰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供骑乘的马,另外如放牧用的马是不需要装饰品的。云南少数民族最早骑马的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时期,那时我国内地正是战车和车战最盛行的时候,不仅战争中没有骑兵,连上层人物出行都乘车,而不骑马。滇国马饰、马具较发达,马镫出现的时间也早,正是云南少数民族骑马历史久远的必然产物。
云南古代民族多骑马而不乘车,马具较齐备,这也和当地多山少平地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就以骑马出行来说,一出门不是上山就是下坡,而且山大坡陡,行动十分不便。如果像恩格斯说的那样:“在较古老的雕塑品上,武士是骑在没有鞍子的马上的”。在欧亚大草原上,骑裸背马也许不太困难,可在多山地的云南就不那么容易。因裸背马上无任何攀系,仅靠骑士的双腿夹紧马腹才不致坠落。此法在平地尚可,骑者在马背上也容易保持平衡,可在山高菁深的云南就很困难了。所以云南古代基本上没有骑裸背马的历史,乘有坐垫马的时间也不长,很快就出现了攀胸、腹带、后鞦齐备的马鞍。也只有这样的鞍具,才适应山地民族骑马的需要。山地骑马和平地不同,不仅要有马鞍和腹带,攀胸、后鞦缺一不可。上山必须要攀胸,下坡要有后鞦,否则马鞍虽有腹带固定,也容易前后滑动,甚至有发生“转鞍”的危险,骑士必然会从马上坠落下来。也许在草原或沙漠地带骑士坠马算不了太大的事故,可高山深谷的云南就不那么容易了,其后果自然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我认为攀胸、后掀齐备的马鞍最先是由山地骑马民族发明的,后来才逐步向平原地带推广。陕西临潼二号秦俑坑出土的陶马上,有腹带、后靴而无攀胸,说明当时内地的马鞍还不甚完备,有无攀胸似无关紧要。
至于马镫,那更是山地骑马民族的发明了。云南少数民族在长期的骑马实践中,发现最困难的问题是骑者在上山下坡时,身体难以保持平衡,即上山时上身必须前倾,下坡时要后仰,十分不便。于是他们在马鞍下系两条绳圈,用双脚的大拇指各伸入一圈,上山时用脚将绳圈蹬向马腹后,下坡时蹬向马腹前,这样骑士上身始终保持平衡,手中的兵器也更能发挥作用。因此我认为马镫的出现最早是为适应山地民族骑马设置的,更确切地说是云南古代少数民族发明的。因为任何一种发明创造,起先都是在条件所迫和力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下实现的,包括鞍具和马镫的发明与改进。因此世界上最早有攀胸、后鞦的马鞍和原始的绳圈式马镫,都不大可能出现在沙漠及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中,尽管他们都有悠久的骑马历史和高超的骑术。因为马鞍和马镫起初都是为适应山地民族骑马而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与骑马历史的长短和骑术的高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至于马镫后来成为许多地区和民族共同使用的一种马具,形状和制作材料上也在不断改进,这当然不是最早发明马镫的云南古代少数民族的初衷。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考古》1997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 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