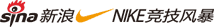龚睿那:退役后事业爱情双丰收 招商工作有挑战
2006年,龚睿那在湖南益阳出任益阳体育局副局长。那里是她的家乡。从此益阳多了一位干练的美女局长。
“打完雅典奥运会,龚睿那找到湖南体育局,希望能安排在省里工作。但体育局希望她打到2008、2009年再退下来,否则只能当湖南羽毛球省队副总教练,没有行政待遇。”作为昔日的教练,益阳体育局局长杨智勇动了心思。2006年,在与当时益阳市委书记蒋作斌的一个饭局上,后者再次提出,“回来算嗒!”“要得。”龚睿那工作的事就这么爽快地敲定了。
龚睿那一直称杨智勇“杨老师”。回到家乡益阳,让龚睿那很安心。从这里,曾走出了唐九红、龚智超、龚睿那等7位世界冠军,被称为“中国羽毛球之乡”。龚睿那的履职,并不是挂个官衔。“在这里,你必须以一个基层工作人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位前羽毛球一姐、世界冠军感叹,“以前是人民为我服务,现在真的是我为人民服务了。”
长沙、北京甚至香港,只是存在于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出差中。家、办公室、羽毛球学校就是龚睿那目前的生活常态:在家带孩子,8点上班,看各种文件,参加各种会议,会见形形色色的人,去各种各样的地方考察,在餐桌上吃花样百出的辣椒。“在这里可以放心吃辣。”龚睿那说。
龚副局长负责的是承办羽毛球世界杯时的招商,以及为益阳羽毛球学校寻找赞助。现在,学校里孩子们的免费牛奶,使用的红双喜球拍,甚至是体育局办公用的电脑,都是她找来的赞助。益阳这座内陆城市比不得长沙,更不要说北京、上海,谈一笔赞助并不那么简单。
“我是红双喜形象代言人。在一次活动中,我对他们的老总说,现在很多基层体校都认尤尼克斯,你们要战胜他们必须从基层开始。”在以自己巨幅画像为背景的益阳羽校训练场,龚睿那透着几分得意和干练。龚副局长目前负责青少年和群体工作,每年有几十万元的招商指标,但她喜欢这种挑战。因为龚睿那正在将益阳和益阳的羽毛球事业推向国际化。
2006年,国际羽坛停办多年的世界杯在益阳重新起航。龚睿那亲赴日本邀请正征战汤尤杯的陶菲克。当陶菲克第一次来到龚睿那的家乡,第一次见到中国五六岁就学羽毛球的孩子们时,一个小朋友好奇地问龚睿那:“我怎么觉得陶菲克长得像外国人咯?”把龚睿那逗得半天直不起腰来。那是益阳这座城市第一次这么向世界开放。后来,当陶菲克在北京奥运会与龚睿那重逢时,开玩笑说,怎么不再邀请他一次?
有儿又有女,高崚有意效仿
全运会团体赛正在激战,湖南队后援团方阵里,一个稚嫩的声音在喊“鲍舅舅加油!”就算还抓不牢手里的加油棒,但谁的热情都没有她高。小姑娘口中的“鲍舅舅”当然就是鲍春来,能与他这么亲近,只因为妈妈是被鲍春来叫做“那姐”的龚睿那。
龚睿那的出现,比当天场上的任何一场比赛都更引人关注。而比龚睿那更受欢迎的,是她的女儿乐乐。全运会后就将挂牌的高崚,第一计划就是生孩子。她希望能尽快完成这个目标,像龚睿那这样已足够令她羡慕。2007年底生下乐乐后,龚睿那又给乐乐添了个刚满五个月的小弟弟。高崚见人就说:“她有两个小伢咧!”看到两个小天使,高崚也顾不上看比赛,就把小家伙抢来抱在怀里。最后留下一摊口水在她领口,高崚还很兴奋。
湘妹子性格泼辣。打球时的龚睿那就被人形容为可以大口喝酒的豪放女子。人们对她退役后的生活有过很多种想象,甚至还有传言她该向娱乐圈发展。但是她闪电般离开国家队,闪电般结婚,又闪电般有了孩子,并且一生就是俩。
“都说女儿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们看像吗?”还未满两岁的乐乐,害羞地躲在龚睿那怀里。被这么多“怪阿姨”围观,乐乐一时有点无所适从。在带乐乐去洗手间的路上,乐乐一屁股赖在地上,就是要妈妈抱。看得出,龚睿那很宠她。
跟大家熟络之后,乐乐活泼的天性又显露无遗。她开始撒欢似地在走廊里奔跑,骗她“警察叔叔来了”也根本不管用,但只要龚睿那一说,“快,鲍舅舅打球了!”爱疯的乐乐就笑着奔回妈妈怀里。“她就不知道什么是怕。”龚睿那解释说,“前段时间小鲍去香港治疗的时候,去我家住过,所以乐乐和鲍舅舅特别亲,是吧?”乐乐这次听话地“表演”了“鲍舅舅加油!”
龚睿那婚后十分低调,人们所知道的就是丈夫比她年长几岁,几乎把她当女儿疼。而乐乐的爷爷是前中国驻欧洲某国大使,家庭氛围极好。龚睿那给乐乐取名禹师睿,带着点女承母业的意思。乐乐从小就在羽毛球场长大,那些世界冠军们不是“舅舅”就是“阿姨”。可是乐乐最喜欢的一个字就是“不”,问她“不什么”,乐乐又笑咯咯地赖在妈妈怀里,扭来扭去喊出了一句:“全部都不!”
四年前, 父母相伴最后一场比赛
四年前,龚睿那在全运会上以一个团体冠军、一个女单亚军结束了她的羽球生涯。女单决赛那天,正是龚睿那的26岁生日,但是她输给了比她小7岁的蒋燕皎。再往前追溯四年,她的师姐龚智超同样是在全运会上以女团、女单两枚金牌辉煌谢幕。她们的故事被拍摄成了电影《闪光的羽毛球》。而没有了她们的湖南女团,在十一运会上已从女团冠军跌至第四。
十运会女单决赛后,球场过道里有些拥挤混乱,被人群冲散的龚求山拿着摄像机,镜头里却找不到自己的女儿。看着龚睿那被簇拥着走进了新闻发布厅,龚求山才最后一个挤了进来,在最后一排座位中间找了个可以把女儿收进镜头的角度。他举着摄像机,想把关于女儿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他拍自己的女儿,拍女儿的对手,也拍在场的记者。他明白,这也许是女儿的最后一场比赛。正因为如此,他长途跋涉,和龚睿那的妈妈邓国珍坐了23小时的火车才赶到赛场。
“我想先给自己放个大假。这么多年没有陪过家人,我想陪爸爸妈妈好好地出去散散心。”台上的龚睿那对着爸爸的镜头笑着说。龚求山将视线从屏幕上移开,父女俩眼神交集的时候,龚求山堆起眼角的皱纹满足地笑了。第一次隔着镜头看自己的女儿,龚求山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女儿的坚强突然间让他感到陌生,更是感动,更是心痛。他关上摄像机,最后一个走出新闻发布厅。在走廊里踱了两步,却发现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最后,一个人孤单地坐到了休息室门口,眼睛却直直地盯着地板。他就这样固执地守着里面的女儿。
龚睿那和全运会是有种缘分的。她最津津乐道的,是1997年八运会女团比赛。实力强大的湖南队在团体赛中场场战至第五盘,作为队中第三单打的龚睿那屡次面临严峻考验。而她次次力挽狂澜,一出场就定乾坤,因此得名“黄金第三单”。与此同时,她也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改名。因为比起她的同门师姐龚智超,“龚睿娜”的名字显得过于柔弱,少了运动场上必需的那股杀气,从此“娜”变成了“那”字。
又一个四年过去,龚求山再次陪着女儿来到全运会赛场。只是这次,他和老伴的主要任务是来散心,并帮着那那照管外孙、外孙女。(本报撰稿 本报记者 邹晔)
网友评论
相关专题:第十一届全运会专题
- 弹指一杯:林丹称帝是中国羽毛球队的悲哀! 2009-10-19 11:15
- 李永波透露羽毛球联赛明年诞生 17支队伍球员千人 2009-10-19 06:14
- 访乒羽中心副主任李永波 全运会推动羽毛球发展 2009-10-19 06:12
- 全满冠林丹仍不满足 热爱羽毛球目标直指伦敦奥运 2009-10-19 06:09
- 视频-鲍春来饮恨林丹成功卫冕 全运羽毛球畅快收官 2009-10-18 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