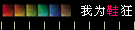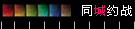垫场赛张喜燕完胜师妹 人生经历比好莱坞电影曲折 |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5年08月22日00:29 竞报 | |||||||||
|
20日晚,中国首届世界职业拳击冠军赛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上演。在首场垫场赛中,集2002年世锦赛和2004年世界杯54公斤级的双料冠军于一身的张喜燕战胜了15岁的小师妹刘畅。 赛后,张喜燕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只是“感觉打得不过瘾,刚活动开比赛就结束了。”在结束了自己的比赛后,张喜燕一直静静地坐在场边观看,不时还比画着拳手的动作,目睹贝凯旭和约翰将女子拳击的金腰带系在腰间,张喜燕很是羡慕。“真是挺羡慕她们
全部比赛结束后,两人又当起了“追星族”,不断找拳王们合影留念。“真是太兴奋了,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今天坐在场边,亲眼看到她们在场上的表现,感觉真好,自己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虽然只是一场垫场赛,但中国拳手张喜燕在这次职业拳击冠军赛中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张喜燕是女子拳坛的佼佼者,但却有着不为人知的悲惨身世。她的经历要比《百万美元宝贝》中的麦琪还要曲折。 张喜燕24岁的哈尔滨姑娘,父母双亡。做过钟点工、服务员、卫生员、护士。只要能挣钱,多苦的活儿,她都抢着干。 1995年,张喜燕走上拳台,10年里,因为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她曾经被迫离开拳台,但追求金腰带的梦想从未放弃。 “我是这么地渴望着,然而我又是一直痛苦地失望着。对我来说,人生本应如此,它给我的更多的是残酷。” ——摘自张喜燕日记 人生就好比一场拳击比赛,充满了躲闪与出拳,如果足够幸运,只需一次机会、一记重拳而已,但首要的条件是你必须得顽强地站着,就像里克尔的那句名言:“没有任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张喜燕就是如此,忐忑命运下她依然挺住了。 中国女拳王: 我不是百万宝贝 女子拳击听起来似乎还有些陌生,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有些残酷,即便伊斯特伍德的《百万美圆宝贝》风靡奥斯卡。但张喜燕却深深热爱着这项运动,而且练出了名堂。 这位哈尔滨姑娘今年25岁,就读于沈阳体育学院,2002年10月27日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女子拳击锦标赛上,张喜燕成为中国队唯一赢得金牌的选手,一举成名。在2003年和2004年的全国拳击锦标赛中,她都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在接下来2004年的世界杯和今年1月举行的挪威杯国际邀请赛中,她又以无可争议的表现成为冠军得主。 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女子拳坛的佼佼者,却有着不为人知的悲惨身世。她的经历要比《百万美圆宝贝》中的麦琪还要曲折。 一家三口 靠100元维持生活 从出生那天起,张喜燕就注定要承受常人所无法承受的悲苦。张喜燕的母亲因糖尿病并发症尿毒症长年卧床不起,剧烈的疼痛,把母亲折磨得瘦骨嶙峋。 张喜燕的父亲原来是八一队的举重运动员,在一次训练中不慎受伤,腿部的血月板进行切除后就再也无法站在举重台上比赛了。随后张父转业回到哈尔滨元件三厂,从一个很有前途的运动员成为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满打满算下来也只有100块钱。张喜燕上学的学费、在学校运动队的训练费、母亲的医疗费都要靠这100元钱维持。 1995年6月5日算是张家的一个转折点,哈尔滨体校招生吸引了张家爸爸。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喜燕说:“孩子啊,爸爸原来是一名运动员,因为受伤不能再打比赛了,爸爸把所有的梦想和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张喜燕虽然眉眼秀气,但打小就剪个寸头,说话直来直去,嗓子粗粗的,连走起路来也风风火火,冷不丁一看地还以为是个男孩子。在报名表上性别一览划上女的时候,负责报名工作的老师就在旁边提醒她,“小伙子,这个你划错了。”喜燕一愣,转而哈哈大笑,“老师,我是个女孩。我要报散打,熟悉之后再练拳击。”这个老师上下打量了张喜燕一番,像是伯乐发现千里马一般雀跃了起来,“真是个好苗子,你别报散打了,像你这种身体条件可以直接报拳击。” 就这样,张喜燕很快地入门学习,练了不到40天,就去参加比赛,而且在48公斤级的比赛中拿了个第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4个月里 母亲去世 父亲病危 1998年11月份,母亲突然病重。 有一天,并不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医院的病床上,母亲的话突然多了起来,好像要把一生的话一口气讲完。“孩子啊,你要听爸爸的话,好好学习,好好训练,好好照顾自己。妈妈不在的时候,天冷了记得多穿件衣服。”妈妈的话给喜燕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她的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更没有这样细心地叮嘱过她。 果真没过三天,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地寒冷,没有了母亲,这个家不再完整。从此以后,张喜燕和父亲相依为命。根据东北当地的习俗,父母去世后,作儿女的要守灵100天。张喜燕怀着失去母亲的痛楚在家为母亲守百天,之后,来不及收拾行李,就回去训练了。 屋漏又逢连阴雨。母亲去世还不到四个月,父亲也突然病倒了。大夫甚至让张喜燕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昔日那个有说有笑的父亲,几乎变成了一个植物人,每天只会吃东西,不能说话,也不会动,眼睛总是呆呆的。邻居、朋友左一百右一千的经济支援帮助父女两苦苦支撑。 这4个月,是张喜燕一生难忘的4个月。 钟点工、服务员、卫生员、护士,拳王的多重身份经济上的压力张喜燕被逼得到处找临时工作。什么钟点工、服务员、卫生员,只要能挣钱,不管多少,也不管多脏多累,她都去做。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这个19岁的小姑娘肩上。 2000年1月份,张喜燕的一个表姐,在医院给她谋了一份差事——给医院的牙科医生当护士,一个月可以赚到300元。听到这个消息,张喜燕想都没想就去上班了,在医院什么活都抢着干,因为父母都生过大病,所以对前来看病的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医院的院长看到眼里,记住了这个男孩子气的女孩,一年后,给喜燕加薪加到550元,这也是张喜燕第一次拿到这么多的工资。每个月有了这几百块钱,父亲的医药费、家里的水电费、买菜做饭的开支就有了保证,喜燕的脸上露出了这一年多来都不曾有过的笑容。 很多次,父亲都问她现在还想不想练拳击,想不想去上学。张喜燕都会说,“爸爸,我现在只想和您在一起,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想。”其实,在喜燕心里,还有那么一丝丝渴望,渴望有一天能够回到学校上学训练,到世界的拳击台上夺冠。张喜燕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是这么地渴望着,然而我又是一直痛苦地失望着。对我来说,人生本应如此,它给我的更多的是残酷。” 恩师相助 重回拳台 希望总是在最绝望的时候站出来给人生的勇气和追求的力量。2001年6月份,张喜燕原来训练体校的张廷芳教练找到了她,希望她能去打比赛。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比赛,两年没打比赛了,张喜燕一想到要比赛心里吃发怵,“我行吗?”而由于长期不训练,体重也增加到了60公斤,比赛级别提高了,难度就更大了。张廷芳赛前给了张喜燕几天训练的时间,但是教练看过喜燕训练就说,“技术不差,就是体力下降了。你没问题的。”在拳击台上,21岁的喜燕又一个真真切切地听到自己久违的心跳声。如此强烈、如此渴望地去奔赴赛场。 正是这次比赛,让她有机会认识了田东教练。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有幸重新回到职业体育的道路,脱离对她来说没有任何体现自我价值的生活。田东教练在哈尔滨成立了一家拳击俱乐部,当时了解到张喜燕的家庭情况,马上又找到了她,让喜燕每天到俱乐部来训练,并且答应每个月给她600元的补助。张喜燕放心不下家中的父亲,接到这个信息后犹豫不决。父亲通过邻居知道这件事情后,把张喜燕叫到身边,对她说:“孩子,你喜欢干这行,爸爸高兴,你还记得当初你刚去体校时爸爸对你说的话吗?你去吧,我现在好多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张喜燕看着父亲坚定的目光,决定去俱乐部。 2002年,俱乐部的田东教练去长春当教练,张喜燕不得已转战沈阳体院。 这一年的5月8日,也成为张喜燕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她一个人背着行李找到了沈阳体院。晚上,在宿舍的台灯下,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心声,“命运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像抓住救命的稻草一样,万般珍惜。我相信一切都是努力的结果,我更要感谢这些帮助我的人,是他们让我获得了新生。” 世界冠军 父亲临终的梦 命运又一次和喜燕开了一个玩笑。距离全国拳击比赛只剩20天,家乡传出爸爸病危的消息。她的父亲第二次脑出血住院了。父亲昏迷了整整6天,第四天的时候,父亲醒来10分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眼睛呆呆地看着病床前焦急的喜燕。张喜燕多么想和父亲说说话啊,“爸爸,你说说话吧!”父亲的嘴微微地颤抖着,好像要说什么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张喜燕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爸爸,你一定要挺过去,我过几天打比赛还要你看呢。你想不想看我打比赛啊?想的话就握一下我的手。”父亲很听话的握了一下喜燕的手。“爸爸,你想不想让我得冠军啊?想的话就再握一下我的手。”这一次,病危的父亲狠狠地握了一下喜燕的手。 张喜燕的眼前一片模糊。 第六天,张喜燕的父亲撒手离开了人世。办理完父亲的后事,张喜燕回到了学校。十几天,张喜燕一点饭都吃不下去,像个傻子一样,常常一个人坐在寝室呆呆地看着窗外,脑子里仅能回忆起的全是和父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小时候父亲给她穿衣服,带她去体校训练,回家和父亲对打练习...... 一个月后,张喜燕又重新回到训练场,2002年8月份,全国拳击比赛,张喜燕以绝对优势摘得女子54公斤级比赛的冠军。半个月后,她入选国家队,在湖北石堰进行了两个月的训练后,随队前往土耳其参加第二届世界女子拳击锦标赛上。而这一次比赛,让张燕喜一举成名。当站在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时,张喜燕哭了,像个孩子一样地哭了。而这次夺冠也为她挣得1万8千元的奖金,用这笔钱还完父亲住院期间欠下的所有的债务之后,她手里只剩下了 700块钱。 张燕喜说她只哭过三次,拿世界冠军是一次,爸爸去世的时候哭了,还有一次是在国家队集训期间过8月15的时候。当时周围的队友晚上都给家里人打电话,自己却没有亲人可以一起过节。“别人都有父母打电话,我却什么都没有。” 文/本报记者 李洁 |
|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