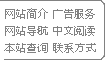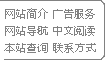今天首次披露40年前中国准备申办奥运会的一个“方
案”,或许可以使读者看到新中国在它成立不到十年的时
候,就已经打算在体育上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思路。
人们由此而可能产生的联想是,倘若我们没有经历“
大跃进”及至后来的“文革”,中国的申办或许会成功得
早一些。但历史不能假设。
40年前第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者对中国,对中国的体
育事业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而更重要的是,将一个充满活
力的朝阳般的新中国通过奥运会展现在世界面前,可以看
作是“走向世界”的思想在当时的一种强烈体现。
申办是国家的意志和行为,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实力构
成其申办的条件。今天,当我们有机会去回顾40年前的这
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它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极为丰富的。
1958--四十年前的一次申办
50年代中国与国际奥委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之初,
我国就非常重视国际体育交往。同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以下简称体总)即宣告成立,取代了原“中华全国体育
协进会”,并组织进行国际体育交往活动。1952年2月5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电国际奥委会,声明将参加第15届
奥林匹克运动会,同时还声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体育组织。同年,体总又致函国际业
余篮球、田联、游联、足联、自行车联合会等,声明“中
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被改组,决不允许台湾盗用“协进
会”名义进行任何活动。体总相继得到国际游联、篮联、
足联等国际组织的承认。
在赫尔辛基奥运会举行前夕,国际奥委会面临着左右
为难的处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台北的“中华全国体育
协进会”都同时宣称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对于人口众
多的新中国和当时还占据着联合国席位的台湾,国际奥委
会都无法拒绝,于是1952年7月17日,国际奥委会第47届
全会作出决议,同时邀请这两个组织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台湾对此提出抗议,没有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体
育代表团因交通受阻,仅游泳运动员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
。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终于第一次飘扬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在实现了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的目的后,我国继续
要求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唯一合法代
表,要求驱除台湾“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54年,在
雅典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以23票
对21票通过决议,同时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华全国
体育协进会。显然,这种决定不能为我国所接受。
1955年,在第51届国际奥委会年会上,我国国际奥委
会委员董守义继续提出对驱台问题进行讨论。由于当时的
国际形势对中国很不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不承认
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而且还支持台湾占据着联合国的席
位,加上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具有强烈的
亲台政治倾向,而对新中国怀有偏见。以上两个因素使我
国的正义要求遭到了国际奥委会的拒绝。
此后,国际奥委会在邀请中国参加第16届墨尔本奥运
会的同时,又邀请台湾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
对此,董守义代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在国
际奥委会执委会和联席会,第52届委员会会上多次提出抗
议,认为这是图谋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但国际奥委
会在布伦戴奇的操纵下,仍然坚持其错误决定。在抗议无
效后,我国被迫宣布不参加墨尔本奥运会,本已集结广州
的运动员奉命撤了回来。
这以后,董守义与布伦戴奇又有过多次通信,但双方
未能就此问题达成谅解,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为了坚决抵制“两个中国”的政治阴谋,维护祖国的
神圣主权,1958年8月19日,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体总
)发表声明,宣布中断同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
显然,台湾问题是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破裂的主要
导火索。
有学者认为,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8月19日这段时
期,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实质上处于“
摩擦阶段”,双方关系发展的道路并非平坦。
寻找四十年前的见证人
光阴荏苒,转眼过去四十多年。当时跟殷传福一起在
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业与民用建筑研究室工作的同事,几经
变动,已分散各处,很难寻觅。
根据殷老先生提供的一份名单,我们与远在杭州市建
筑设计院任总建筑师的程泰宁取得了联系。接到我们千里
之外的电话,询问四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程老先生显得有
些激动:“那是很久远的事了,电话里这一句两句的也说
不清楚。”与殷传福在接到设计任务之前对奥运会及奥林
匹克运动还闻所未闻不同,1956年毕业于南京工业学院的
程泰宁,此时已经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规模宏大的体育盛会
———奥运会。所以,在他负责设计中心体育场时,首先
就想到了在大门上得有一个五环标志。而他自己能成为这
项大工程的设计者,心里感到十分自豪,特别珍惜这次机
会。当时年仅23岁的他日夜加班,为主体育场设计倾注了
极大的心血。
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程老先生一说起当年的事
情,脑子仍很清晰:“当时的形势要求我们什么都要成为
世界第一。一个三十万人的体育场,在设计时立即要解决
的就是这么多观众观看体育比赛的视线和结束之后的疏散
问题,为此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试验。现在想起来,
当时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项任务、一个概念去完成,而没
考虑其它方方面面的事。不像现在,我们申办的各方面条
件都成熟了许多。”在殷传福提供的名单中,还有赵宝馥
(当时负责看台布置研究)、蔡体芳(当时参加总体设计
工作)、姬星洲(当时是规划设计的组长)、谢光昭(参
加视觉质量研究和中心运动场设计)。但记者多方打听,
还是没能找到他们的下落,真想听听他们年轻时候参与这
项伟大工程设计的感想。
我可以证明:新中国曾有一个梦想
殷传福,65岁的中国石化北京工程公司高级工程师,
是他率先投书本报,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40年前,一个
鲜为人知的申办奥运会的举措曾在北京悄悄运行。
1998年11月25日,北京正式向中国奥委会提出申办2
008年奥运会。听到这个消息,殷传福心里一阵激动:在
经历了1993年申办失利的痛苦之后,我们终于再次向世界
发出洪亮的呼声;而中国人要办奥运会的梦想,早在40年
前就开始了酝酿,殷传福就是当年仅有的几个这一梦想的
规划参与者之一。
当本报记者登门采访他时,殷传福激动地说,我可以证
明,早在建国之初,伟大的中国人民就胸怀着为奥林匹克
运动作贡献的抱负。并不是现在日子好过了,才想起借奥
运会振兴体育、宣扬中华。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眼光,在那时就盯住了国内建设之外的领域,瞄准了
最能振奋人心的奥运会。
那是1958年的秋天,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在为重
庆建筑大学)毕业才两年的高才生殷传福,被组织上安排
参加“国家体育场”的方案规划设计工作。刚刚24岁的他
担任该项目总平面设计项目的负责人,与其它几个人一起
被当时的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请去听介绍及汇报工作。
于是他知道该体育场是为了北京申办1968年奥运会而准备
的场地设施,而且是在兼任体委主任的贺龙副总理亲自过
问下进行的。
当时国家体委基建财务司邀请了建设部建筑科学研究
院(原建筑工程部建筑科研院)、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原
建筑工程部工业建筑设计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参
加“国家体育场”的方案规划设计。由于正值迎接国庆十
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高潮,所以真正投入总体
方案规划设计工作的是殷传福所在的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工
业与民用建筑研究室。
这项设计非同寻常,尤其对于初出茅庐的殷传福及他
的伙伴们来说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们努力工作
,没有一天是在半夜12点以前收工的。好在都是单身汉的
他们无所挂牵,办公室、宿舍就在上下楼,连轴转的成果
就是一个星期拿出设计图,近一个月场馆的模型都出来了
。由于那时他们对奥运会这样规模的体育盛会在头脑中还
没形成什么概念,又不能出国进行什么考察,所以只能到
图书馆查相关的资料。“国家体育场”的设计主要是参考
莫斯科列宁体育场的布局,而有关立交桥在主要交通路口
及地铁快速疏散大型文娱场所人群方面的设计思想,也是
得益于国外相关报刊的信息。
在北京选址的时候,考虑了两处建设用地:一处是在
复兴门外五棵松路北,另一处是在颐和园旁边的西郊机场
。由于五棵松规划用地小、离市区较近,设计人员担心用
地面积不够,几十万人一下子涌出赛场,很容易造成交通
拥堵,所以都比较倾向于选址西郊机场。但据说当时主持
国防部工作的彭德怀元帅考虑到西郊机场的军用价值,不
赞成把机场改作他用。为了保险起见,设计人员完成了两
处用地的三个方案,即:五棵松一个;西郊机场作了一大
一小两个方案,小方案是怕占机场地盘太多通不过而设计
的。
按照当时有关领导的要求,中心体育场要建成世界上
最大的,要超过1950年举办过世界杯足球赛的巴西里约热
内卢市马拉卡那体育场。殷传福说:该体育场是世界上最
大的,能装22万人,有17万个观众席(现据资料显示:马
拉卡那体育场能容纳20.5万名观众,有15.5万个座位;
当时最大的体育场是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斯特拉霍沃体育场
,1934年建成,能容纳24万名观众,场内可进行4万人的
团体操表演)。所以我们的中心体育场设计容量是30万人
,其中看台一层100排共15万座位,二层60排共10万座位
,场内可容纳5万人活动。“那时在大跃进形势的激励下
,提出这样过热的设想是很容易理解的。当时有一句口号
就是‘二十年超英赶美’,我自己就被请到河北徐水县去
设计20万头规模的养猪场,还到山东为某公社设计百米宽
的大道和社员大楼。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种设想确实有
点不切实际。”在设计期间,国家体委主要由基建财务司
的一位副司长具体与设计人员联系,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交
换一位意见。没过多久,由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坚持“两
个中国”的错误立场,我国退出了国际奥林匹克组织,这
项为申办而进行的“国家体育场”设计工作也随之偃旗息
鼓。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因为有关方面想通过斗争再在国
际奥委会争取到合法的席位。所以1959年在北京举行的第
一届全运会时,体委基建财务司给我们送来大量的体育比
赛票,希望我们能熟悉各个项目的特点,为今后的设计作
准备。
殷传福回忆道:“大概到了1960年,我们的设计工作
才完全停了下来。前后共一年多,我们室参与此项设计工
作的不到10人,全中国知道当初我国想申办奥运的人可能
也超不过100人。”殷传福认为,当时的设计方案,将直接
牵动首都的整体规划走向,其规模所吸纳的物力、财力,将
影响到几年的中央财政预算。殷传福坚信,这么大的举动
,一定获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首肯和支持。
殷传福说:“在当时,办奥运会不像现在这么热门。
各国申办奥运,也只是为了显示国力,为体育运动作贡献
,结果常常是付出得多,得到的少。只是近几届奥运会广
告、转播权收入猛增,特别是对举办地后续发展的推动作
用,为申办才这样争得你死我活。”谈到假如中国在196
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能拿到1968年的奥运主办权,我们有
没有能力在当时的条件下把奥运会办好时,殷先生认为,
以当时“内事服从外事”、“经济服从政治”的原则,中
国不仅能办奥运会,而且会办得很好。1960年中国在经济
最困难的时期,还成功地举办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就是个
有力的佐证。他设想,假如那时中国申办成功,就不会有
十年浩劫;借奥运之机敞开的国门,就会使改革开放的大
好局面早点呈现。在1959年第一期和第六期的《建筑学报
》上发表的《运动场视点和视线高差“C”值的研究》、
《运动场视觉质量的研究》及《公共建筑人流疏散的计算
问题》三篇文章,就是设计人员在为“国家体育场”工作
期间的设计和调研论文,也算是当年申办奥运留下的一点
历史痕迹。再后来,殷传福根据他们设计研究的成果,在
1962年11月2日的《体育报》上发表了一篇《选择看台的
学问》。
在此之后,殷传福的工作与体育再也没有联系到一起
,但他对体育工作倒存了一份关心。他注意到当时为建设
“国家体育场”而划出的五棵松用地,直到北京亚运会建
起奥体中心之前一直没动,而现在亚运村附近又辟出一块
空地。他据此以为,举办奥运会是40年来中国人心中的一
个长梦。面对北京的再次申办,殷传福不由得感叹:“从
1958年到2008年,50年的期盼,但愿美梦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