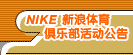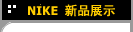新浪体育讯 我从事高山探险事业已有31年。高山上壮丽的风光深深吸引了我,使我虽屡经千辛万苦,也舍不得离开这个行业。经常周旋在各种各样的自然危险之中,也不止一次与“白色死神”--雪崩擦身而过,我暗自庆幸:除了冻掉二节手指头外,还没尝到“死”的滋味。然而后来我还是和死神见了面,被活埋在雪中又神奇般地被战友抢救出来,成为登山队中遇到同样遭遇的众幸存者中的一员。
1984年9月,我被派与武汉地质学院和十七名师生一起和日本长野县登山爱好者去青海省的阿尼玛卿第二峰进行登山训练。在那难忘的登山活动中,大自然的狂暴与宁静、迷人的美景和迷宫似的复杂地形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中日两国运动员之部的友谊、欢乐与歌声伴随着我们。生活是那样的充实、紧张。而最令人难忘的却是九月十一日的一场大雪崩。
这天早上,我们中日双方11人从冰雪覆盖的5200米出发,虽然遇到了不少地形上的困难,中午1时半还是到达了5700米的高度。这里有一条宽约3米、深不见底,长约两米的大裂缝。我们在裂缝边休息了一上多小时,吃了干粮,准备将营地建到更高一点地方以利攀登顶峰。
三点四十分,日方三个队员还在休息,中方八人先出发了。我们从左侧绕过大裂缝,爬上一条漫长的缓坡,进入宽广的冰雪平台。前方可以见到阿尼玛卿峰与四峰之间的山脊鞍部两侧是雪坡。我们完全置身于冰雪世界之中,高原上的阳光本来就十分强烈,经过冰雪的反射,更烤得人脸上火辣辣的难受。积雪有四十多公分厚,每踩下一步都深及膝盖,走起来相当费力。我一直在前面开路。陈建军和我一个组,紧跟在我的后面。他的体力技术都较好,万一我开路时有什么危险,他是完全可以保护我的。我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没有后顾之忧。为了照顾我,队员匀背了不少装备、器材、食品。我的背包里只有一台小型摄相机和两台照相机。我一边走一边想:肩上的担子实在不轻,中方八人除我和陈建军之外都是新手。这些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高山适应性不错,体力也好,年纪又轻,就是技术很不熟练,带着他们上山处处提心吊胆。在山下我很少管他们,上山后却管得很严没有少说他们。我这个结组除小陈外,还有常林昌和包得清两个学生,他们一步不拉地跟在后面。由李致新、熊继平、刘强和王勇峰组成的结组距离我们约30米,在雪坡上缓缓行动。
下午四时,我们到了5800米,我们正处在三面都是冰雪围绕的谷底中心,前方有一堵45度的冰雪坡,高约三百米,一直通向鞍部的山脊。再有200米就要爬坡了,我决定在这儿休息十分钟后来,大家都感谢这短暂的停留十争钟,我们距离雪坡远了一点,否则的话……
日方的丸山和女队员下山真理技等三人从后面赶上来了。他们要到前面去开一段路。他们三人结组从我们身边穿到前方走了20多米后,开始向右上方斜切。这时,我们结组也开始跟着他们的脚印前进。天气是那样的晴朗,四周是那样的洁净,自然界安静得让人吃惊。只能听到大家费力的喘息声和积雪被踩下去的“沙沙”声。
突然“轰”的一声,在宁静的气氛中如晴空霹雳。我抬头一看,不禁大叫一声“雪崩!”只见前面二百多米高的地方,群山仿佛被拦腰截断,一只整齐的横向断裂出现在三面冰雪围墙之上浪花般的积雪翻滚着从山坡上向我们俯冲而来。“将冰镐插进去,固定自己。”我呼叫着。日方三人向右侧疾步奔跑。
小陈在我身后大叫:“快跑!”可是,几个人被结组绳联在一起,脚下又是深雪,跑起来谈何容易。我还未跑出两步,齐腰高的雪浪已涌到我面前。腰下感到巨大的压力将我向后推去,双腿顿时动弹下得。这时,小陈在我右后方用全力拉了一下结组绳,我横着凌空翻了个滚,爬在滚动的雪堆之上。在我滚动的时候,好象看见小陈也仰面朝天倒下去……
我还没喘过气来,第二个冲击又袭来了。这次比第一次还要凶猛,时间相差不过五秒钟,浪头大致有二米高。我被裹进了翻滚的雪浪之中。再也听不见战友们声嘶力竭的呼叫声,再也看不支他们的身影,向边只有雪粒翻飞的沙沙声。一股雪凶猛的涌进我的嘴里,几乎将我窒息。我不由自主用双手护住面孔,用力向外推雪,力图保留一点空气。好在终于被我挤压出一个洞,我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这时,雪崩后的滚动已经停下来,我知道雪崩已经过去。但愿不要来第三次冲击了。此刻时间似乎停滞了。我如同一条小鱼被冻结在冰中,脸朝下腰被压得弯曲难受,只有两只手还可以动。我竭尽全力臣自救,但无希望;想在大口的喘息中平息一会儿,也是徒然。空气越来越少,头脑开始发胀。“完了”两个字向我袭来。我不知道自己被埋了多深、埋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同伴们的情况。四周静得可怕,我感到自己可能要在这寂静中离去,不是窒息而死,就是冰冻而亡。
拼命挣扎了五分仲左右,忽然用手捅开了雪层,一片亮光照在我布满冰雪的眼镜片上。空气流通了,我暂时死不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战友来救,来拉我来把。忽然,我听到有人在叫喊。那喊声分不清楚是什么,但分明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呼喊,隐约中可以听出李致新那焦急的嗓音。我想喊叫,但喊不出来。原来我在翻滚中腰上被结组绳不知缠了几圈,这时可以感到腰上的绳子一阵比一阵地拉紧,快把腰勒断了。这不是在救小陈,就是小陈在找我的信号。我抓住头上的红色太阳帽,从小洞中全力向外扔了出去。事后才知道,这帽子为寻找我的战友指明了我遇险的具体地点。
当雪崩袭来的时候,最后一个结组的四个队员侥幸没有被埋上。雪波与他们交臂而过,当他们发现前方的队员不见了时,全惊呆了。待定下神来,一切已恢复平静。雪崩来得凶猛,停得突然。王勇峰、李致新、刘强、熊继平四人发疯般地向上爬,边喊带叫向刚才还有人的地方奔去。先将常林昌、包德清拉了出来,顺结组绳又挖出了陈建军。小陈埋得很深,出来时都立不稳,由于缺氧脸色铁青,头脑发胀,痛得要命。正当大家心急火燎地顺结组绳挖时,忽然从雪堆中飞出一顶红帽。李致新一下扑到帽子前,拼命抓住了我的一只手:“可找到你了!可找到你了!”“怎么样?”“都出来了!”“日本人呢?”“出来了。”“好!”凭感觉,我知道这时王勇峰、熊继平也都在我上边。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将我挖了出来。我部起来,浑身不停地找哆嗦。刚把眼镜片上的雪擦掉,只见日方古急切地招手。我脑子里“轰”的一下,“怎么回事,你们快去看看。”王勇峰等四人连跑带爬地向古留站的地方奔去。原来下山真理枝只露出个头部,身子全埋在雪里,呼吸异常困难。等到把她挖出来时,已神志不清。我们把她扶着装到睡袋里边同用结组绳捆住她的腿。迅速向雪坡下撤去。提赶快离开雪崩危险区。回到大裂缝边时,我们围在下山身边,给她擦手臂、身体。一会儿,下山哭出来了。这就好了。一小时后她完全恢复过来,不断地用日语感谢大家。我们这支小分队,在倾刻之部被雪崩打得七零八落,依靠集体的力量,只用了十分钟时间,全体脱离了危险。
说来也巧,雪崩开始时,正是与大本营联络的时间。大本营的同志只从报话机中听到我们喊“雪崩”两字,以后山上音讯全无。顿时,营地中平日的欢笑、打闹一扫而光。等到再次出现讯号后,我们已全部脱离危险。
粗略计算,这一次雪崩,大致崩下了三十万立方米的积雪。
隔了一天,我们又一次穿过这曾充满惊心动魄的地方,胜利登上了阿尼玛卿Ⅱ峰6268米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