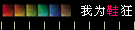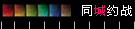在老房子中寻根 |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5年11月18日10:09 中国体育报 | |||||||||
|
我家以前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所处的位置,现如今可算得上是上海市的黄金地段,周围新建了好多摩天楼,每平方米均价已卖到4万元以上,可是老房子至今还没有拆迁,听说是区政府有意保留那一片老宅,于是我兴起再回去看看的念头—— 没想到,在老房子寻根时我竟然心跳加速,满腹惆怅。
我家以前居住的位于上海黄浦区广东路352弄4号的老房子至今还没有拆迁,那里可算得上是真正的市中心黄金地段,周围新建了好多摩天楼,每平方米均价已卖到4万元以上。听说是区政府有意要保留那一片老宅,旧上海称广东路叫五马路,上海开阜初期的妓院主要集中在宝善街(今广东路东段)。1910年版《上海指南》中说:“野鸡多在福州路(旧上海称福州路叫四马路)胡家宅、南京路(旧上海称南京路叫一马路)香粉弄一带,到了清末民初,这里已形成以福州路会乐里和广东路群玉坊为中心的妓场,其中会乐里内公开挂牌营业的妓院达百余家之多。故上海人又把四马路、五马路称之为“红灯区”。 我家老房子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盖的一家下等旅馆,二层楼。解放后,住进28户人家,这以后,婚嫁娶配,繁衍子孙,成了近40户。每户住得像豆腐格子般很小,中间一层薄板相隔,讲话嗓门一大,隔壁听得清清楚楚。人口增长后不够住,就捅天花板搭阁楼,几乎家家都有能睡人却直不起腰来的矮阁楼。 楼上楼下各有一间15平方米的厨房,几十户相挤一处。几十只煤球炉齐烧,温度最高时达50摄氏度以上。厨房内每户各拉一盏电灯,开关却装在各自家里,电线密密麻麻像蜘蛛网。灯泡有白有黄有红,晚上,几十盏灯齐亮,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新结婚又添了一户人家,实在没有地方安放煤球炉,经居民小组会议讨论,就将煤球炉安置在楼梯半当中的拐角处。 大门口共有七个水池子,一家一个水龙头,一根总水管上来,曲曲弯弯水龙头一长串。因为怕别人家偷水,每家的水龙头上还都上了锁,大锁、小锁、插锁、挂锁、铜锁、铁锁,各姿各态。 倒粪便,要提着“马桶”走出弄堂,跨过马路,拐个弯,再钻进另一条弄堂。于是,常有偷懒者半夜里掀开大门往阴井盖倒粪,一路上粪便四溢,使夜归居民踩一脚屎尿。我们有时候跑出约1里路去延安东路上厕所,免费的,早晨时大部分时候会遇上排队,每位蹲厕者身边都排着两三位“客人”。谁要是碰上拉肚子便急,那只能求爹爹告奶奶,即使如此,具有菩萨心肠的好人也不多,常有老人或小孩急得拉一裤子。隔壁邻居比我小一岁的女孩李丽就是因为将屎拉在裤子上而得了个外号“漏斗”,这不雅的外号一直跟着她从小学到中学毕业。 走廊,本来就不宽敞,每户各霸一段,破椅子、旧盆子、烂席子堆得满满实实,几十家几十年的“垃圾宝贝”都堆在那里,有几处,身子胖一点的人非侧着身子才能勉强通过。几十家的二三十辆自行车全都停在大门外,窃车贼光顾了不知多少次,可居民们还是只能把车停在大门外。 整幢楼的内部采光就靠天井顶棚十几扇玻璃窗,窗子太高,窗上的尘埃几十年来几乎没有认真擦掉过。居委会曾组织人用六七米长的扫帚扫,怎么也扫不干净,用水冲,楼下人家家家进水,因此,楼内这么多年从没见到过鲜亮的阳光。 每家都烧煤球炉子,每个月的薪水刚到手,主妇们油盐酱醋之后的事就是奔煤球店补充燃烧“能源”。“煤球卡”上的煤饼额度不够用,就买些煤粉回家自己做煤饼。“工地”就在楼下,零件是煤、水和煤饼机。煤饼机是个铁家伙,搁入一半湿软合适的煤粉,用带孔洞的手柄压下去,然后用力提上来,转向,重复刚才的动作,一个湿的煤饼就做成了。工序的要点在于压得紧,否则松松垮垮的,煤饼尚未现世,就“粉身碎骨”了。煤饼做完后,黑漆漆一列排在墙根晒太阳,等干了以后才出得了火。 夏天,房间里太闷热,有时候热天的晚上我们都睡在大街上。太阳刚下山,各家的孩子就到马路上去抢地盘,拎一桶水把地浇湿,扫净。上街沿上,一段一段铺满了各家的草席。我们就在马路上下棋、打牌、讲故事、看月亮、数星星。半夜里,伴着满街的汽车喇叭声和各种嘈杂声,我们竟也能睡得着。 老房子紧挨着仁济医院,每次救护车警铃声响起,我们都会被吵醒,翻个身,继续睡。清晨4点半,倒马桶的车摇着铃经过,将我们吵醒,再无睡意,正好起身去菜场排队买菜。 楼梯口的王家姆妈五口三代挤在12平方米的朝北偏房里。螺蛳壳里摆不了道场,王姆妈就在宽不过1米的楼道里动起了脑筋。放皮鞋的纸箱搬上了走道,脸盆架子接着登场,后来,老太太的米缸竟然搁到了邻居家的门口。 在王仁和食品厂看门房的大柳伯伯居室只有楼梯旁边的3平方米,身无长物,仅有一张小床和小桌,外加一只煤油炉子可煮口饭烧口茶水。室外阳光灿烂的日子,室内幽暗得必须开灯照明。大柳伯伯终生未娶。 刘阿姨生9个孩子,一家11口人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吃饭、睡觉、做功课都在一间屋里。做功课,一张小凳子就是书桌。吃饭,各找各的地方。最难的是晚上睡觉,下面一个铺睡几个人,房顶搭了吊铺住几个人,一个长桌子上也睡人。 我的表叔,16岁从河南来沪,在八仙桥菜场摆修鞋摊16年,每晚在他哥哥家(就在我家楼下)地板上过夜。1969年他娶了老家的姑娘为妻,他到房管所要求租一间房。房管所所长告诉他:“你看上海哪里还盖得下房子?不可能的。”表叔只好打道回府回了老家。 老房子邻里间的“战争”常年不断。 弟弟有次冲开水,不小心把水洒在地上,水从地板裂缝中滴了下去。楼下人家在吃饭,水正巧滴到饭桌上,他们破口大骂起来,硬说是弟弟把痰盂尿倒了下去。隔壁“来发嫂”帮助鸣不平,楼下人又诬陷说是她指使弟弟倒痰盂尿的。一气之下,来发嫂真的端起一痰盂尿扣在楼下人家门板上,一场厮打由此开始。住在大门口的“好婶婶”出面劝阻,结果连她一起挨打受骂。好婶婶怒火中烧,干脆搬个方凳坐在大门口歇斯底里地骂了起来,翻出十八年老账,恨哪家骂哪家,谁去劝就骂谁,派出所也拿她没办法。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调查研究室主任陆晓文曾做过一个社会调查:私人领域越小,其公共领域的空间越容易受到私域的侵占,从而引来邻里纷争。 我搬出老房子已20多年,老房子周围几乎全部成了高楼大厦,每到夜晚灯火璀璨,老房子还是那么拥挤不堪,连安装空调机的地方也没有,各家的煤球炉如今都换成了管道煤气灶,可是有的老年人还是习惯用煤球炉,习惯于自己做煤饼,说是这样更省钱。楼上楼下,各家摆了好几张麻将桌,整幢楼里,有的开电视,有的听广播,有的大声训斥小孩,再加上“哗啦哗啦”的打牌声,炒蚕豆一般滑润脆亮,一点也不寂寞。好婶婶也还在,好婶婶的丈夫几年前突发脑溢血去世。弄堂口,一位老伯坐在小凳子上,剪着指甲,一片金黄色的阳光暖暖地照在他身上。 老宅的弄堂里多了一扇大铁门。老宅旁边的“浙江电影院”还在,我几十年里至少在那里看了几百部电影,至今还在正常播映。格致中学阔气多了,把周围整条马路上所有的旧房子全部拆了,东南西北,浙江路、北海路、广西路、广东路,四四方方,一个学校占了好大一片,校舍造得金碧辉煌,像五星级宾馆似的。因为是“市重点中学”,受到区长和市民另眼看待…… 故地重游,回味当年的生活,感慨万千,别有滋味在心头,对今天的生活更加知足、珍惜。 |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