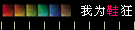陈露:冰上蝴蝶,回来了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5年01月10日07:18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 |
|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深圳华润万象城,刚刚矗立起来的一个mall,在顶层,一个滑冰场已经进入最后的装修阶段。正像接待我们的华润的陈先生事前所描述的,这是一个专业的,设施、规模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称得上是一流的冰场,而且,巨大的玻璃屋顶可自然采光。想象着在冰的冷静和阳光的热情中翩翩起舞,真是让人充满向往。 为了这个美丽的冰场,陈露回来了。 没有人会忘记1996年长野冬奥会上,陈露在做完最后一个动作之后长跪冰面痛哭的情景。在此之前,陈露获得过世界花样锦标赛的冠军,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的最好成绩。而在随后的比赛中,她的名次却跌落到了第25名,甚至差点无法获得参加奥运会的资格。期间她经历了换教练的风波,经历了伤痛、发胖等等对于一个运动员的困扰。陈露把长野冬奥会当作是自己的告别表演,因为她实在是太疲惫了,这个性情女人在痛痛快快宣泄以后,就退役去了美国。陈露说,那会谁要是说让她练,哪怕再坚持一年,她就和谁拼命。 陈露说,过去的一切,是成长的代价,她没有后悔过,只是现在想来,会有一些遗憾,如果有些事情不去经历的话,也许她的运动寿命会长一些。所以,她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悟传授给后辈,她把她这几年在美国的漂泊也当作是一次学习和积累,她的心里,随时准备着归航。 所以,这次和华润合作的“陈露滑冰俱乐部”,可以说是陈露多年梦想的一次完美实现。“冰场刚刚浇上冰的那一天,真是兴奋,我和伙伴们上去滑了一圈又一圈,舍不得下来。”陈露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几年过去了,陈露还是那么美,虽然那天她穿得很朴素,也没怎么化妆,只涂了睫毛膏,睫毛长长的、密密的,毛茸茸的一双大眼,晶亮晶亮的,扑闪着,还像小女孩一样可爱。只是她在给自己的学生做完指导后,对我们说“还是小孩,说了老忘,老不改”时那种严肃的语气和神情,才让我们感受到陈露的成熟和身份的转变。“以后我要培养的不是陈露第二,而是绝对要超过陈露的人。” 陈露这只美丽的冰上蝴蝶,还要继续飞。 小时候,我喜欢滑冰 滑冰真是太辛苦了,半夜练习,冻得裤子都解不开,得尿裤子 记者(以下简称“记”):刚才看到的这个冰场太漂亮了。 陈露(以下简称“陈”):是呀,这个冰场实在太好了。好多人看了都说一定要摸摸这个冰,因为在南方很少有这么大的一块冰,北京也挺少,东北多一点。 记:谁都没想到滑冰这个项目可以在南方开展。 陈:冰上项目其实是室内项目,和地域没有什么关系,都是人工制冷,应该和经济条件有关。其实东北现在也不在室外滑,但我小时候练滑冰的时候条件差,只有在室外滑,而且是半夜,因为小嘛,好的时间要留给大队员。相当冷,零下40摄氏度呢。 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爸妈舍得让你练啊? 陈:我滑冰是很自然的。我父亲是冰球教练,母亲是打乒乓球的。我从小住在体育学院的大院里,周围都是教练。我小时候就喜欢跳舞,但身体不好,当时两个姐姐都在滑冰了,所以就当锻炼我的身体,爸爸给我借了一双冰鞋,让我跟着姐姐滑。上到冰上去以后我特别喜欢。父母其实不太希望我搞专业,知道这会很苦。当时体操队也要我去,妈妈说我们可不练这个(笑)。滑冰滑得好一点以后,我就开始参加比赛,成绩总是比同年龄人好。一般正式进专业队应该是14岁,我被特批,12岁就进去了,后来到国家队,我比教练的工龄都长(笑)。现在想起来,滑冰真是太辛苦了,半夜练习,冻得裤子都解不开,得尿裤子;鞋带也系不上,鞋带就老丢,妈妈就给我准备了一大卷鞋带。后来父母还半夜起来帮着我系鞋带。所以,最后能坚持住,其实是家长坚持住了。记得那会冰鞋的刃坏了,每天爸爸给磨刀,磨两个小时,手都磨出了血。当时主要是我喜欢,他们就付出心血来培养。那个时候家里都挺穷的,但还是买了录音机,每天放音乐,让我跳舞,找感觉。后来攒钱买了录像机,爸爸把那些好的跳跃动作都编辑起来,让我看。 艰难的世锦赛冠军 在国外训练,枯燥,又受伤,还挨打 记:你是练着练着很自然就走上了专业的路,那什么时候开始对拿冠军有期望了? 陈:小时候在专业队的集训队,我觉得拿个全国冠军就很了不起了。后来在少年组拿了成绩以后,我看到很多世界冠军都是先在少年组拿了冠军,就想:“没准我也能!”妈妈说:“你好好练吧!” 记:你应该知道花样滑冰不是中国的优势项目啊。 陈:我知道滑冰不是中国的优势项目,我们的选手出国都是倒数第一第二。我当时想,拿到全国冠军就了不起了。我第一次参加世界少年比赛就拿了铜牌,也没觉得挺难。小时候滑冰就觉得开心,那么多小孩一起玩。我喜欢比赛,人来疯,比赛有吃好的,有奖品,那会儿全省比赛的奖品是文具盒,红色的围巾,我拿去学校炫耀。 记:你一直觉得滑冰是个好玩的事情。 陈:到十五六岁才发现不好玩了,太辛苦,在国外训练,枯燥,又受伤,还挨打。这和我们国家的教育方式有关,所谓严师出高徒。那段时间太痛苦,但是想着放弃了又可惜,毕竟练了这么多年了,我又是中国最好的,大家都对我怀着期望。也不想跟父母讲,怕他们担心,但我确实发自内心地不想练了。本来滑冰是我心里最喜欢的,但却挨打。有一次到北京集训,下了火车,太疲倦了,还发烧,但是快到全国锦标赛了,下车就去练,练了下来,人都不行了,走路都走不了了,高烧,头疼欲裂,还吐,住院以后诊断是心肌炎、脑膜炎,其实就是疲劳过度。咱们的训练手段还是大运动量那种,其实花样滑冰要有力量基础,但是技巧性更强,需要表现力,人老挨打,情绪压抑了,还怎么去表现?还有,国内的教练永远觉得你不好,永远觉得你达不到要求,所以你总是没有信心。其实表演是一种情绪,动作到了,情绪不到也不行。而且教练管很多,我最喜欢长头发,不喜欢短头发,小时候妈妈为了我漂亮都没有给我剪,教练却老是要我们都剪和她一样的短发。后来到美国,我去表演,教练不怎么管我,我反而释放了自己,以前一直压抑的东西就恢复了,将真正的自己表现了出来。 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1995年还是拿了世锦赛的冠军。 陈:本来1994年就该拿,但那个时候受伤了。受伤也是训练方法不科学造成的,到世界锦标赛的时候就不行了,后来走路正面沾地都不行。比赛是比三项才算总分,不比放弃又可惜,离冠军这么近了。那时候什么药都不管用了,就打麻药。最后预赛的时候要打6针,结果痛点越来越多。在候场时有很多摄像机,我就跑到洗手间哭。日本医生看了以后说:情况很严重,是疲劳性骨折骨裂,很有可能一个用力骨头就完全断了,比赛就不可能参加了,以后手术都不可能痊愈,就算痊愈也难恢复,要保守治疗,就要放弃比赛。结果队里开会,决定放弃这次比赛。 记:运动员受伤恢复以后的训练是比较痛苦的,你怎么样啊? 陈:那时候天天躺在床上把脚举着。放假是我梦想了很久的,但真正休养了,心里又不踏实。那时候我身体正好在变化,长高了,整个感觉不一样了,恢复的时候,完全是从头练的意思。刚开始我没底,一个多月以后感觉又找来了。其实避免严重伤病是有办法的。 那个赛季我没有参加比赛。我鼓足勇气给教练讲,想留头发。教练用特别不可思议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说:“那不好看的话还得剪。”我心里暗自高兴,心想,留长了怎么都不剪了。我还打电话告诉了妈妈。到世界锦标赛,我整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了,成熟了,不是小孩了,很多人都没有认出我来。我整个人有了新的面貌,也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这次比赛,在编排上采用了更多我自己的意见。以前是被动的,给我一个动作我就做,现在我可以说我喜欢这个,我想要这个好。不过那次比赛还是不顺利,遇到拉肚子,幸好到决赛时恢复过来,越比越好。拿到冠军以后我很高兴,毕竟那一直是自己追求、梦想的东西。 换教练闹风波 我特别伤心难过,有段时间就回家了,一下子胖了10公斤,没办法训练了 记:拿了这个冠军之后,结果因为换教练闹了一场风波,是吗? 陈:从这次比赛到长野奥运会之间,我跟教练的分歧越来越大。在中国,教练就是上帝,但我和国外的人接触多了以后发现,对他们来说,教练就是要帮助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不具备这个能力,你可以换教练。结果我想得简单,国内的人对此都不理解。这时我的教练已经没有把时间花在我身上,本来每天有3个小时的训练时间,这时只有1个小时了,其他的时间她去教美国学生。我希望在技术和难度上有突破,她已经给不了了。我没想到一下子就是一个大的风波。 记:有人说你忘恩负义,得了冠军就换教练。 陈:各种说法都有。其实我完全可以去滑职业赛了,那样可以赚很多钱。我是中国运动员里第一个有经纪人的。但是我希望能拿世界冠军,能拿奥运会冠军。既然还想提高,就只有换教练。 记:当时是什么感受 陈:那些说法出来以后我特别伤心难过,有一段时间就回家了,一下子胖了10公斤,没办法训练了。后来1997年世锦赛时我回国家队,一个月里要减10公斤。这次比赛也是奥运会预选。太辛苦了,饿得痛苦,看人都离远点,看谁都像鸡腿。可是那次我掉到25名,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当时我自己也觉得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心都凉了。后来教练就走了,去美国了。 记:教练走了,你怎么办? 陈:这样就换了教练,是黑龙江的刘宏云教练。刚开始我很辛苦,情绪特别不稳定,老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笨?生气,着急,特别敏感,谁说一句什么话都能刺激我。接下来的比赛要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参加最后的奥运会比赛。从小到大我没体会过比赛 害怕的滋味,那次是第一次体会到。教练开导我,给我讲故事,我特别感激他。那么短的时间内,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我们能配合得那么好,最后才拿到那个成绩,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的沟通,他费了很大的心思。我记着刘老师最常讲的一句话:“露露,你放心,比好了算你的,比不好算我的。” 记:这么大的压力,而且还有失败的可能,为什么非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陈:其实名次不重要,重要的是去证明自己。不服气啊!我觉得一直支撑我走下去的,最主要的还是我自己的信念吧。我觉得我还没有把我自己所有的能力发挥出来,我还要继续坚持。就是这个目标支持我一直往前走。那时候说什么话的都有,等着看热闹的不少。 记:现在可以理解你为什么在比赛完以后痛哭了。 陈:是呀,那会儿才觉得完全释放,之前我简直要崩溃了。太痛苦了。那会儿谁要让我坚持一年我就要和他拼命。虽然说那次没能拿到冠军,很遗憾,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人生而言,应该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 异域的另一种生活 最主要的就是孤独。搬家的感觉挺可怕的。一直以来我都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说,有个家。 记:对你去美国为什么很多人会存有争议呢? 陈:那个时候我提出转业,一些领导觉得我真的是练得很辛苦,既然她想退役的话,我们就尊重她的意见。那个时候不也是说来去自由吗?但还有一些领导觉得,现在我的技术状态又回升了,那我应该继续为国争光为国努力。就是这两种不同的看法。 记:你自己的态度很坚决吧? 陈:那会儿是身心疲惫,累得要崩溃了,就去滑“职业”了,换换环境。 记:换了一个环境,怎么来适应在异域他乡开始的另一种生活? 陈:好像最主要的就是孤独。第一年,应该是最不适应的一年,什么东西都要你自己去做。没人管了,人就觉得特空。那种环境下,人最害怕的就是生病,一生病就更痛苦,感觉是雪上加霜。我记得有一次,两个朋友说去我家买菜做饭。那时候我有点感冒了,不是很舒服,但也没当回事,跟她们转了一天。后来她们说:你发烧了,烧得脸都红了,去医院吧。我们三个只有我有驾照,只有我有车,我就迷迷糊糊地开着车,她们给我指路。到了医院候诊,那个医生说没事,发烧,打一针就好了。那个医生特好,是一个老头儿,看着特慈祥的样子。然后,我抱着老头儿就开始哭,就觉得特委屈。特别想家,想家只能打电话,所以我每个月电话费都特贵。那个时候电话费一个月近1500美金。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这钱必须得花。 记:除了孤独就是搬家? 陈:嗯。搬家的感觉挺可怕的。我一开始住在旧金山,从旧金山搬到纽约,从西海岸搬到东海岸。我在纽约住了半年,又搬回西海岸,搬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在凤凰城还算待得长,两年。然后我又搬回纽约了,又在纽约住了一年。现在我又搬了,搬到马里兰。我是在横跨美国。这种感觉很不好。一直以来我都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说,有个家———不管我走到哪儿,最后我都想回到这儿,这儿就是家。但是现在很难讲,因为要从工作上考虑。年轻,占第一位的肯定是自己的事业,所以就不能更多地去选择。 记:你说过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你就会回来。 陈:一直想回来,在国外一直觉得不是最终落脚的地方,是在学习。现在这个机会可以说已经等来了。我们的冰场已经做好了。我希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教给队员,让他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记:我们都知道你和俄罗斯男友的浪漫爱情,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花样滑冰运动员,你怎么说服他放弃在美国的事业来到中国? 陈:说来就是他要选择我还是选择美国的问题,他当然选择我。在美国他教的学生已经拿了全国少年冠军,所以他要放弃很多跟我来深圳。他来这里也是做教练。 本报记者孟蔚红文/图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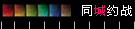 |
|
||||
|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