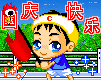以黑夜的方式观看(下)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10月09日09:50 南方都市报 |
|
一角度 如果能以一句话概括,那么,吴虹飞的歌属于女性被压抑的欲望以扭曲方式的极度膨胀。一方面是因未遂而被抑制的、极少极少的情欲,一方面是扩张和膨胀的、末路狂花的野蛮贪心,这形成了幸福大街上最奇特的一道景观。幸福大街有一部分力量来源于青春少年对夸张事物的热爱,如同男孩对暴力的推崇,女艺术家的背叛之途有时难以免俗地源于女孩对 妖邪、凄丽的着迷。但仅仅说这些也还是不够,我们必须得说起黑夜,说起月亮姐姐的热病。“我十九,一无所知/谁能料到我会发育成一种疾病?”1974年,女诗人翟永明曾在她长诗的开头这样自问。女人内部有一个黑夜,而黑夜的内部是一个深渊。黑夜的意识,惨无人色的内心,就像一个秘密的约定,无比古老;多年以后,我们又开始在吴虹飞的歌里看到这一切。 十年前一度引起震动的女诗人唐亚平的黑色诗,拿来描述吴虹飞,居然也会是那么贴切,虽然后者入境还并不深:我长久地抚摸那最黑暗的地方/看那里成为黑色的漩涡/并且以漩涡的力量诱惑太阳和月亮。 确实,这也正是吴虹飞所做的。用女人幽黑的洞穴,吸附和涡旋起尘世的一切;用女人眼睛后面的眼睛,学会以黑夜的方式观看,这正是她们所做的。把每一个日子都变成黑夜,把每一个时辰都变成患白血病的月亮孤独照耀的时刻,正是女艺术家所为,是女艺术家们的专长。 回到矫揉造作还是真实的问题。现在让我来展示另一部分答案,这部分的答案是:真实。 人是最奇特的事物。当你回答人是已知的,他有巨大的不确定,大到比你知道的一切都大;当你以芸芸众生为答案,她不屑地走开,走到世界遥不可及的暗面。而艺术家的人生轨迹恰恰是,从俗人的身份起身,从矫揉造作起身,走向你最终可能把握不定的地方。 身体可以改造,人性可以冒险。大脑和心灵中的未知领地很大,它像一片亘古如今的荒原,被正常生活、健康心智、道德公理等阻隔,滞留在普通的人生履历之外。对内心世界而言,人这种东西可以任意地捏造、修改、畸变,从此进入秘密洞穴,进入黑夜之门,在另外一个世界中把人性的隐秘一一尝尽。刚刚踏入之时,这初学者难免是矫情的,但人竟可以被这虚无幻境滋养、融化,渐渐变成远方忠诚的儿子、心语人生的忠实仆人、意识深处无尽奥秘的守护者;而再不只是繁华街市的市民,敦厚民风中的老百姓。艺术最终成为本能,远离常人的轨道,打开了一切。 幸福大街的乐器库曾经摆满各式兵器琳琅满目,现在倒变得简单了,变得一目了然却卓然。配合着吴虹飞,他们现在只是简单地动动手,轻描淡写却意蕴深远。乐手们在走向成长。 吴虹飞也在走向成长,虽然她过分自恋,但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吴虹飞越来越深地触及到女性内心的体验,创造出具有女性性征的独特艺术形象。属于吴虹飞的道路,处于《女儿》、《一只想变成橘子的苹果》、《流氓》所铺设的路标之间,而不在早期貌似更深沉的《四月》、《嫁衣》、《刀》、《夜》或者好像更有风格的隐藏音轨《现场》之中。《现场》是装出来的,《四月》、《嫁衣》是摹拟物。吴虹飞从没有真的哭泣,她只是模仿哭泣,只是被那魔幻般的气氛一时迷住了。矛盾也不是她自身的问题,只是她特别喜欢矛盾令人着魔的效果。吴虹飞并不是纤弱女子,她的个性实际上相当硬朗。死亡、阴冷、癫狂、歇斯底里、深沉、凄厉、悲凉、惨烈,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突如其来的乖张情绪、令人惊惧的高音发作、惨烈的嘶喊和大气的阴暗之歌,其实都是别人家的物事;午夜绽放的妖花、灿烂绝望的神情、疯了似的没人腔的哭喊、色彩艳丽和凄凉的故事、极致悲楚顿挫的美,究竟只是看来的风景。那只是个入口。从那里进去,吴虹飞发现了傻妹妹的痴癫发情,憋不住的、高兴的反讽,笑嘻嘻的黑色幽默和反淑女做派的率真直露,从这些地方,吴虹飞真正揪住了创造的一点皮肉。 这几首吴虹飞最难听的歌曲,成为她特别有趣的、充满灵感和创造力的时刻。《女儿》和《一只想变成橘子的苹果》,女童的尖脆叫声居然是情欲,是嗷嗷的情逗和性调侃。《流氓》还惊人些,泼妇式的刺耳谩骂,闷声的发狠哭嚎,掩藏的却是温柔依人的柔情和痛彻子宫的哀痛情歌。它是最吴虹飞式的。最接近她本人的气质——灵巧机智,世俗、温良又刻薄,爱煞出风头和反弹琵琶之事。我毫不怀疑吴虹飞的未来,她的未来应该就在这里面。 李皖 |
|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