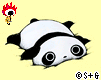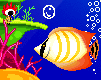| 瞭望东方周刊:“跛足”的中国体育何去何从? |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08月09日14:39 中国新闻网 | |||||||||
|
74岁的北京市民张海森,每天早上都会来到南二环广安门立交桥下跳健身操,已经坚持了7年。 在这块有4个篮球场大小的椭圆形空地上,每天早晨都聚集着五六十位晨练的老人。离他们几米远就是早高峰繁忙拥堵的二环路,车流喧腾,尾气浓郁。
张大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和他一起锻炼的老人中,有的已经在这里坚持了10多年,因为“实在没有其他合适的地方”。 看看周围密密麻麻不断拔高的写字楼和住宅小区,张大爷很纳闷:怎么就不能稍微留出点绿地,“谁都要喘口气嘛!” 在这个4年后即将迎来奥运会的超大都市,能容纳8万人的体育场已经在几十公里外的城北开工;而像张大爷这样见缝插针、呼吸着汽车尾气锻炼的人们,不知还有多少。 遥望2008年举全国之力铺排的体育盛宴,今天的诸多不协调实在很是刺目。 “跛足”巨人般的中国体育,曾经作为中国计划经济和陈旧体制的典型而屡遭诟病,但它似乎还要在畸形制度的推动下坚持走到2008年。那么2008年以后又怎样呢? “举国体制”何去何从 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亦即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下俱乐部制的以国家财政拨款、以各级政府力量包办体育的机制,因为其纯正的计划经济“血统”,在改革开放后颇受争议。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多位体育研究专家表示,举国体制对于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有限的资源办好奥运固然有效,但中国业已启动的体育体制改革却必然因此而放缓,许多矛盾都可能被忽略或掩饰。 曾在体育大省辽宁多年执行举国体制的国家体育总局官员崔大林说:“我个人预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许会成为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全国体育工作者殚精竭虑的目标一定是本土扬威,2008年之后,市场化的进程也许就会进入快车道。” 有的学者的预测更为大胆:2008之后,主掌中国体育界半个世纪的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可能被裁撤,各运动协会将迅速走向实体化。“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体育总局这样的机构,一般都是在主管青年或教育的部门设一个几个人组成的委员会。” 占据整条体育馆路的体育总局及其下辖机构,是国务院所属各部委中“体量”最大的。尽管在60多家部委、机构中排名接近末尾,体育总局却保持着特殊的地位。“有哪一家像我们这样,在国际上硬碰硬地为国争光呢?”局长助理肖天自豪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952年比照前苏联模式成立的国家体委,据说在1997年一度被撤销,划归文化部,但在1998年又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其间,运动项目开始协会化、实体化改革,管办分离,陆续成立了20多个运动管理中心,对应同领域的运动协会。但由于被称作“二政府”的中心仍保持行政机构性质,既有垄断地位又面向市场,协会有名无实。 肖天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现在,举国体制在体育领域占据主流。如果中国的体育体制完全仿照西方俱乐部制,中国的竞技体育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但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早在1988年的《兵败汉城》中就尖锐地批评道,中国体育的最大悲哀便是“衙门化”。更有业内专家说,体育界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自足的官僚体系,思想保守,观念落后,既得利益者很难自主启动改革。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举国体制是非常态的,是特殊时期的短期行为。省市的尖子队员抽到国家队可能坐冷板凳,浪费资源,这种增量发展是粗放式的,浪费严重,广种薄收。 熊晓正认为,对于运动员的培养,可以用政府向社会采购的办法取代从小培养、常年训练的大包大揽方式。 肖天则说,专家建议的方式还不到实行时候。尽管足球、乒乓球等都在搞俱乐部制,对原来计划经济形成冲击,“但量并未影响到质”。 他说,体育总局正在尝试把一些项目放在有条件的省市体育系统去办,“2008年奥运会可以切三分之一的项目给地方”。 但肖天表示,他并不担心2008年后竞技体育会“树倒猢狲散”,竞技体育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影响力依然存在,“何况任何改革都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状况相匹配”。 而着眼于奥运战略,举国体制仍然被强调。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近期多次讲到,举国体制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的问题。 异化的体育人 体育总局科研所的研究员李力研,5月间参与筹备了一次国际会议,邀请3位国际一流的教练,为中国体育支招。 让他颇觉尴尬的是,在国际一流教练与中国地方教练的对话会上,许多教练尽管有不少问题想问,但是根本表达不清,“一位田径教练用了5分钟来陈述自己的问题,还是没说清楚”。 经常到运动队调研的李力研说,不少运动员文化水平很低,认字认半边,比如“祈祷”认作“斤寿”,最爱看的是动画片。一位正在某知名高校就读的奥运冠军,念起文章来白字连篇。 这位体育专家说,本届奥运会中国的主要对手德国,没有划艇国家队,运动员仅在出征前一个月集中训练,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手很容易消化教练的训练计划,“而跟我们的运动员讲血液含氧量、乳酸、负荷量,他们根本听不懂,只能是原始性的训练”。 “从1200多人的国家队到20万重点体校的学员,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光中,每天五六个小时的训练让他们没有精力学习。即便成了世界冠军,也是‘半拉子富有者’,是被异化的人。”李力研说。 新中国建立以来累计退役运动员总数高达27.9万。在这个群落中,没有学历、谋生技能又一身伤病的人们,迅速跌落为社会的弱势和边缘人群。 2003年,据媒体报道,曾在中国举重史上创造了40个全国冠军、20个亚洲冠军的“亚洲第一力士”才力,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前国脚唐全顺,因赌球被拘。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才力和唐全顺们,其实是举国体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非正常者。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关键是要建立更为科学、人性化的运动员培养机制。 他说,我国90%以上的运动员是从少儿开始投入专业训练,运动训练中常用的手段是“时间战”和“消耗战”,以“苦”为常态,片面地延长训练时间以增加负荷。“运动员每周要进行30-40小时的训练,再好的体制也无法让他们还有时间和精力完成好学业。” 相比之下,拥有36万大学生运动员的美国全国高校体育协会明文规定,运动员每周训练不得超过20小时。 钟秉枢说,“时间战”和“消耗战”致使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运动员群体出现较高的运动损伤比率。羽毛球国家队队员的伤病率是100%,2001年青少年羽毛球队的伤病率几乎是200%,42名集训队员查出83处伤病。“这使运动员容易对训练产生厌倦,在取得一定成绩后就早早退役。” 以山东省为例,田径选手60岁以下死于心脏病的占总死亡人数的56.26%;排球为62.53%,举重为67.12%,而40岁至60岁的退役足球运动员心脏有疾患的达到100%,这些数字大大高于常人的比例。 “对比我国体坛常见的‘流星’与国际体坛常见的‘常青树’现象,可以想像这给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浪费。”这位专家说。 2001的一项调查表明,高收入家庭不愿意孩子从事运动训练的比例高达77.8%,中等收入家庭为74.6%,低收入家庭也达69.8%。在不支持原因的调查中,64.3%的家庭怕影响孩子的文化学习。 从“工具”到“玩具” 2000年6月,当了12年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卸任后回到湖南老家。他说:“我当政最大的遗憾是人民的体质改善得还不够快,日本人的体质提高得比我们快,二战后他们的平均身高增加了12厘米,而我们还不到4厘米。我这1.68米的个头,回到家乡居然算是大个子,太不像话了。” 与倾尽资源、有超前发展之虞的竞技体育相比,群众体育却是极不相称地落后。 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介绍,2000年的群众体育调查显示,中国的体育人口比例为33.9%。这意味着全国有4.4亿人每周锻炼3次以上,每次锻炼超过30分钟。 但专家说,这个数字并不说明问题,远不能与新西兰93%、日本80%、欧洲80%以上的体育人口比例相比。在统计中,解放军也被列为当然的体育人口。 李力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体育人口中老年人偏多。数字显示,体育人口中,71-75岁的占该年龄总数的46.1%;16-20岁的青少年占该年龄段总数的31.8%;41-45岁的仅占该年龄段总数的6.7%。 “更重要的是体育人口的心态,多是被动性的,不得病不会进行体育锻炼。”李力研说,体育锻炼应该是人的幸福指标,成为人生的重要内容,这才是高质量的体育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覆盖人群最广的国民体质监测2000年完成,结果让人亦喜亦忧。青少年儿童的平均身高、体重、胸围等指标都迅速升高,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身体素质的大幅全面下降,肺活量继续下降,速度、耐力、柔韧性、爆发力、力量指标齐齐下滑。与身体素质下降相对应的是近视的居高不下和肥胖。 几年前,日本新日铁工人与宝钢工人举行了一次大比武。中方卫生人员透露,在同样的技术熟练程度下,我方5个工人比不过一个日本工人,主要原因是体力不足。新日铁工人下班后有规定,必须在工厂的健身房中锻炼一个小时,许多人自觉地超额锻炼。 “奥运经济也应该算一算,每个劳动者通过体育投入在体质体力上有多少提高。”李力研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中国各类体育场馆的数量已超过61万个,人均体育场地近1平方米。但2000年选择在马路边锻炼的人依然达到40%。专家说,这些体育场馆,67%是教育部门所有,25%为体委等系统所有,封闭在高墙之内,只在统计数据上有意义,而仅有8%的“其他”部分可供普通百姓使用。 “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有实际意义的社区体育场地,2002年人均只有0.006平方米。”李力研比画了拇指大的一块地方。 多位专家表示,中国的专业竞技体制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意志化和政治功能化的工具,作为阶段性行为,迟早要改变重心,向休闲娱乐领域转移,成为满足中国人现代精神文化需求的“玩具”。 而从“工具”转变到“玩具”,核心是观念的变革,如何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需依靠人文观念的提升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作者:程瑛、舒泰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