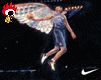要搁中国,艾德沃卡特死都不会服气,自己好不容易才把一支两年前还没份打世界杯的球队辛辛苦苦带进欧洲杯四强,却仍然如此不招人待见。
艾德师傅虽然腋窝不再狂出汗——这个生理特征已经比大多数西人更接近中国人了,虽然可能比大多数中国教练学历高,但他显然还是个东方文化的门外汉。比较显而易见的是,他不可能在对瑞典或者葡萄牙的生死对决前,如戚务生般吟出“宁可轰轰烈烈死,决不
窝窝囊囊生”之类的壮丽诗句,他也不可能体会得到“背城借一”“愚公移山”这种潜藏在貌似温文尔雅的古典中国哲学表象下的凌厉杀气。他是个好日子过多了便腐朽的,正无可挽回地老去的没落的老派欧洲男人。
马龙-白兰度饰演的大多数角色都有能力把荷兰队调教到克鲁伊夫和我等唯美派球迷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的。也许是鬼使神差,上周五晚,我在家里浩如烟海的影碟中随手抓出马龙-白兰度晚年作品《这个男人有点色》重温了一遍,那个以唐璜自居的年轻人以其致命的浪漫情怀击中了马兰。白兰度饰演的心理医生,当然,“也击中了我”。几个小时后,我就看到20世纪最伟大的男主角带着差不多一亿人民币的债务黯然去世的消息。
马龙-白兰度饰演的大多数角色都有能力把荷兰队调教到克鲁伊夫和我等唯美派球迷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的。也许是鬼使神差,上周五晚,我在家里浩如烟海的影碟中随手抓出马龙-白兰度晚年作品《这个男人有点色》重温了一遍,那个以唐璜自居的年轻人以其致命的浪漫情怀击中了马兰。白兰度饰演的心理医生,当然,“也击中了我”。几个小时后,我就看到20世纪最伟大的男主角带着差不多一亿人民币的债务黯然去世的消息。第二天,我在平时最喜欢的一份日报上看到了相关报道。我怀疑这组稿件的作者和编者都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因为内文居然有这样的句子:“1954年 和 1972年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称号是马龙-白兰度最荣耀的时刻”——如今好像只有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才可能坦然说出势利得如此彻底的话来。但他们大错特错了,马龙-白兰度作为男人的荣誉的巅峰,恰恰是他在1972年以一颗悲天悯人之心拒领俗不可耐的奥斯卡奖,他通过那个印第安小女孩传递了爱,愤懑和对世俗荣光的唾弃。
与马龙-白兰度同理,对阿里来说,加冕拳王只不过是帮助他成为黑同胞中先富起来的人,拒绝去越南当炮灰才是他荣誉的巅峰;对项羽来说,率领子弟兵横扫秦军只是若干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中的一件,“不肯过江东”才是他荣誉的巅峰;对普希金来说,写诗和占有整个莫斯科的美女都算不得什么,抱着必死之心接受丹特士的决斗之约才是他荣誉的巅峰。这个世界虽然市侩,但还算公平,公平的法则之一是:你要站在荣誉的巅峰上,就一定要舍弃一些凡人的欲望。所以大多数我认识的人谈起就要曲终人散的欧洲杯,都会说没什么意思,太多球队把决定战略走向的主教练宝座交到像艾德沃卡特等庸人的臀下,他们总想面面俱到,在一些形而下的诱惑中患得患失不离不弃,连最低限度的“悲歌一曲从天落”都做不到,哪里还谈得上意思,没有意思,又何以教人挂怀?
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点价值观层面的东西了,比如:不能给看客和时间留下美好记忆的人,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和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前些天无意中发现一则关于萨达姆的新闻。这个伊拉克前暴君在狱中及之前的逃亡中,居然随身携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居然还在写作自己的第四部小说。看来,这家伙还不是那种完全不可救药的浑球。茨威格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立传时写过一句很酷的话:“在恐惧中默念伟大,在黑暗中默念上帝”。不知萨达姆读《罪与罚》,感受到的是恐惧,还是黑暗?
我得承认,这句话的标准汉语译文是“在恐惧中想象伟大,在黑暗中想象上帝”,我觉得在茨威格的语境中,“默念”比“想像”更生动更有语感,就自作主张把它改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