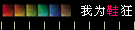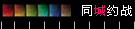| 11年沧桑多少承诺成泡影 艾冬梅誓将官司进行到底 |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6年09月22日11:39 东方体育日报 | |||||||||
|
专题撰稿 本报驻京记者顾晨 东拼西借交纳5100元诉讼费后,海淀法院终于以民事侵权正式立案,原告之一艾冬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们既然走了法律程序,就肯定会进行到底。”当事另一方王德显则愈加神秘,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王德显坚持沉默不语,甚至拒绝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只是表示由王姓代理律师负责此事,“一切到法庭上再说。”
我们毫不怀疑,公道自在人心,公正自有法律。而我们更关心的是,错综复杂的细节之后,25岁的艾冬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体制力量让她从一个贫苦的农村女孩跑向马拉松冠军?什么样的利益机制让她从冠军沦落为双脚严重残疾、每月只能拿三百块的少妇。在这样生动乃至残酷的事实背后,曾经多次为国争光的中国中长跑运动面临的现实处境又是怎样?希望在艾冬梅的人生标本中,我们能寻找到一些线索,尽可能靠近事实的本来面目。 没想过靠跑步吃饭 却成了专业运动员 “小时候就是喜欢体育,跑着玩,也没想要靠这个吃饭。”艾冬梅抱着六个月大的孩子,坐在零乱的客厅一角。这是位于北京郊区通县艾冬梅三叔的家,她和队友郭萍从黑龙江进京讨说法,暂时寄居在此,两人在门厅里支起钢丝床,使原本不大的室内更显逼仄。 艾冬梅老家在黑龙江依安县,父母、大她两岁的哥哥和她,一家四口一直生活在依安镇上。从小爱蹦爱跳的她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靠跑步获得了第一个冠军,“当时县里运动会,我一下就拿了3000米的冠军。”依安镇小学一位姓绳的体育老师,看出了她在中长跑项目上的天赋,县运会后就把她招进校队。“当时我的学习成绩都不错,训练也不重,不是说天天跑,就是比赛之前集训一段,和校队练一下,完了就参加比赛。”年幼的艾冬梅并没有清晰的人生方向,也没想到今后的命运之路会和跑道重叠,她只是感到跑步让她快乐、充实。 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艾冬梅一直在依安镇小学,读书为主,跑步为辅,其间发生的一次“破纪录事件”让她至今记忆深刻。“我那年创造的3000米纪录,现在还是依安的纪录。”谈及此事,她言语中露出一丝轻快,“也是县里运动会,3000米我跑了10分26秒,而原来的纪录是11分50秒,我整整快了一圈的时间。裁判们都不相信我的成绩,非说我是漏跑了一圈。那怎么办?最后就说重跑一次!”次日,憋着一口气的艾冬梅一个人在空旷的跑道上狂奔。“第二天的天气比前一天差远了,又下雨,又刮风。”即便如此,艾冬梅还是以10分50秒的成绩完成了这场一个人的战斗。看到秒表上确凿无误的时间显示,谁也不再怀疑这个坚韧且极具耐力的女孩了。 1993年,艾冬梅马上升六年级,哥哥已经进入初中,同时读书的两个孩子让艾家更加面临经济上的窘迫,生活的压力成倍增加。“原来我父亲在镇上的砖厂工作,母亲是在食品厂,总算还能支撑我们兄妹,但差不多那两年,他们都下岗了,是当时第一批下岗的,后来就只能靠平时打零工来赚钱。”第二年,由于长跑方面的特长,成绩不错的艾冬梅还是升入了齐齐哈尔地区的体校,“那时候每月要交90元食宿费,还有30元管理费。”虽然事隔多年,但艾冬梅对于120元的数目念念不忘,因为这个数字让这个双下岗家庭更加感到了生活的压力。 就像所有类似的故事一样,生活的艰难让艾冬梅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家庭和自己的处境,但当时年仅十三四岁的她并没有把跑步当成人生的资本。“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读完体校就算中专毕业,然后回县里去学校当一名体育老师。”现在说起来,艾冬梅仍然很羡慕那样一种待遇,“是国家正式编制的老师,当时一个月就能拿六百多,现在至少一千多,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啊。”但单纯的教师梦很快就被更强烈的吸引所掩盖。 “95年的时候,黑龙江体工队来地区挑人,体校的老师就说,你有长跑方面的天赋,可别耽误了,能往上走就往上走啊!”在这样一种“人往高处走”的传统信念的刺激下,艾冬梅还是选择了成为专业运动员的道路。当时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食宿免了,体工队负责。”对于当时的选择,艾冬梅看来有些后悔,“当时读完体校直接当老师,就好了,现在也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领完奖 王导就把信封拿走了 对于艾冬梅来说,1995年的那几步,有些急促。进入黑龙江省体工队只有三个月,她就面临一个更艰难的选择。“05年11月,我们在山海关集训,王德显的队伍也在那里训练。有一天,体工队的赵教练来找我,说火车头体协的长跑队和王教练要我们。”艾冬梅说,当时她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很愿意去,毕竟离家越来越远。但随后黑龙江队和火车头队两方都劝说艾东梅等人,“赵教练以前也是王德显的学生,她说那边看上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训练刻苦,意志品质好,有拼搏精神。” 王德显从黑龙江省体工队出来之后,进入火车头体协组建中长跑队,四处寻觅人才。“马家军”放弃的选手,是王德显重点挑选的对象之一,孙英杰就是他从中挑出的璞玉,各地体工队特别是黑龙江队则是火车头寻找人才的另一源泉,艾冬梅、郭萍等人都是由黑龙江体工队转到火车头体协中长跑队,这也就是艾冬梅所说的“我们”。对于转到火车头队的前景,艾冬梅清楚地记得王德显的“许诺”:“他说只要你们练好了,就能转正,成为铁道部的正式职工,管分配工作,还开工资等等。”这些条件中,分配工作最被艾冬梅看重,也成为目前她们和王德显诉诸法律的直接原因。 艾冬梅和郭萍相信了王德显教练的“许诺”,认为可以通过刻苦训练和比赛,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出身和命运,就来到了山海关的“王家军”基地。“夏天4点半,冬天是5点,我们就出操训练,主要是辅助的放松,跑一跑,8点左右回去洗刷吃饭,上午训练一般从9点到11点,回去就切菜,吃饭,下午有休息的,也有加练的。”如果不去外地比赛训练,艾冬梅们就在山海关基地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样的作息,“五年没怎么回过家,电话都没打。”和长期集训并存的,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管理模式:教练亲戚组成管理层、拳脚式的管教。艾冬梅和郭萍不愿意多谈,“这些和工作奖金都没关系,我们也有压力。” 按照艾冬梅的描述,1999年之前没见过工资,“最早说的工资一月一千多,但后来都说用在营养费上了。当时就给我们些零用钱,有时候一月给一百,有时候两月。”直到退役前的2002年,21岁的艾冬梅才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工资存折,“之前一直由王德显保存,他说我们年纪太小,由他代管。”对于数额更大的比赛奖金,更是“一分都没有拿到过”。听到这样的陈述,后来成为原告代理律师的许子栋都很难相信,他让艾冬梅等人详细开列一张收入清单。根据这份清单,艾冬梅作了简单解释:“99年北京国际马拉松冠军奖金10000美元,去掉税之后是8000美元,即使上缴火车头体工队一部分,那剩下来也应该按规定由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半分。王教练说,我们一部分的钱要用做营养费、训练费什么的,其他的由他保管,退役的时候给我们,但我至今没有拿到!”类似的例子还有大连马拉松赛、日本千叶马拉松赛、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北京公路接力赛等,艾冬梅说她在这些比赛获得了从冠军到第六各种名次,但没拿到一分钱奖金。有一个细节让她至今难忘,“乌鲁木齐比赛拿了冠军,奖金装在信封里,直接发给我们,我从领奖台上下来,还没打开信封看,王导就过来拿走了。” 八年比赛获得的奖金,艾冬梅估计至少有二十多万人民币。但目前严酷的现实是,即便她描述的完全属实,由于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已经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追讨。让她感到悲愤的是,除了一两百元零用钱,这么多年只拿到“一笔将近两万元,全都用在治疗上的!”艾冬梅找到北京一个著名的中医骨科大夫,“一个疗程需要两千元,做了六七次,医生当时就说,再不治就彻底废了!” 穿凉鞋 成了种奢望 在艾冬梅等人状告王德显的诉讼嚗光之后,代理律师许子栋的小灵通几乎成了媒体热线。除了代替艾冬梅等人发出维权诉求外,许子栋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作为运动员,她们为国家出了力、为地方争了光,付出十一年的青春和汗水之后,得到的竟然是贫穷和伤痛,她们实际上比那个冠军搓澡工还要不幸。”如果说没有分到胜利奖金、工资“被占”都只是物质上的暂时缺失,那么肉体上的伤病则逐渐消磨着艾冬梅、郭萍对于生活的希望和锐气。 1999年是艾冬梅运动生涯的高峰期,她获得了大连国际马拉松、北京国际马拉松的冠军,日本千叶马拉松的亚军。在运动成绩爆发的同时,她已经开始感觉到脚趾钻心的疼痛。事后她仔细分析:“刚进入体工队的时候,我们骨骼发育还不完全,大运动量的训练,就经常使我们的脚趾疼痛不已。为了快出成绩,队里给我们注射止痛针,从而导致了脚趾严重坏死。现在已经不能长久行走,更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每当说起脚伤,艾冬梅总是掩饰不住的悲伤。 2001年,艾冬梅的脚伤经常发作,她意识到必须停下训练,好好治疗。通过朋友介绍,艾冬梅在北京找到一个著名的中医骨科大夫,“一个疗程需要两千元,做了六七次,医生当时就说,再不治就彻底废了!”为了能够真正地治疗,艾冬梅向王德显要钱,“分了好几次取的,前后将近两万元,都用在治疗上了。”尽管如此,由于脚趾畸形严重,因而很难根治,“医生说最好的情况也就是维持现状,不再恶化。” 和艾冬梅相比,郭萍的脚伤更加严重,由于伤病恶化,她于2002年提前离队。在艾冬梅三叔家接受媒体采访时,当着大家的面,郭萍脱下了脚上的鞋,露出几乎让人无法想象的双脚。五个脚趾不是在同一平面上,其中两个被挤到了前面,而脚掌中上方的那块骨头凸出几乎形成一个直角。“我现在就是一个残废。”郭萍捏着变形的脚趾头说它们没有任何知觉,其中两个畸形的脚趾已经接近“死亡”。 脚伤之后,郭萍她们就没有穿过凉鞋,家里放的就是几双没有品牌的运动鞋。“我现在看人就忍不住看她的脚,我可想穿凉鞋了,大夏天的还要穿运动鞋,好多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个女人了。”郭萍说由于自己在入队时骨骼发育尚未完全,再加上高强度的训练,她十个脚趾中的六个都已经严重错位:“从2001年起骨头开始慢慢变形,疼的时候打一针封闭,好了再练,疼了再打,最后脚烂透了,骨头变黑了……”郭萍说她现在站着或者走路半个小时就累得不行。“我今年都27岁了,还没有男朋友。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这双破脚。”郭萍说。谈过的三个男朋友,在看到她的脚趾后都离她而去。“我不怪他们,谁愿意娶一个过几年就要坐轮椅的老婆呢!” “二十万买断” 又是空头支票 2003年,艾冬梅决意要给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一个句号,她需要为自己的未来盘算一下。 “最基本的就是一份工作,能够保障日常的生活。我们没有文化基础,脚也不能长时间站立,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份可以坐着的工作。”为此,退役前后,艾冬梅曾多次找过王德显。据她说,退役之前王德显曾表示已经把她的关系落到哈尔滨铁路公安处,但后来没有实现。“2004年奥运会之前,我专门到五大连池找王德显,他说工作落实不下来,干脆给二十万元,一次性买断。”艾冬梅说,当时她一想,觉得能够拿到这笔钱,自己就可以“做点小买卖”,也就答应了。“没想到,奥运会结束之后,王德显说这事只是他这么想,体协不批,他也没办法。” 为了能找到赖以生存的饭碗,退役两三年间,艾冬梅在老家依安和北京之间辗转。“最早在老家学过电脑,文秘班那种,但我们的文化基础太差,电脑又是以英语为主,确实很难学完整。”艾冬梅向记者描述寻找一份工作的艰难,“后来又在依安帮人卖手机,也就是几天吧,就干不下去,没办法一直站着。”过了不久,她又来到北京打工,曾经在柜台做销售员和衣店的导购。“但由于脚上有伤,每项工作都干不长,这都没超过两周。”艾冬梅说。前后几次工作尝试下来,她总共才赚了不到六百元。 和艾冬梅类似,1995年入队,2002年因伤离队的郭萍退役后只找过一份工作,就是在家乡某小学当体育老师,每月500元,因为脚伤,“一个小时后,他们就让我下岗了,我就再也没有工作过。”如今,艾冬梅和郭萍都处于无业状态,而从今年9月开始,火车头马拉松队下发给她们的工资从每月700多元无理由地变成了300元出头。最终和她们一起上诉的李娟情况稍好,目前在北京一家商场打工,但她也无奈地表示:“上班才一个月,为了打官司已经请了五次假,希望这事能早点结束。” |
|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