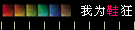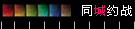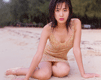国青结束世青赛留下问号一串 谁妖魔化了克劳琛? |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5年06月27日09:24 东方体育日报 | ||||||||||
在输给德国队之后,克劳琛在接受采访时还再次强调:“我是德中足球促进协会的雇员,我今后的工作要听从他们的安排。”这种三角关系的最好例证就是中土比赛前,克劳琛返回慕尼黑接受当地电视台的采访,因为这是劳顿巴赫亲自打电话要求的,而作为德中足球促进会雇佣的克劳琛无法不听从雇主的指挥,尽管从内心里他也不愿意前去。可以设想,如果是中国足协直接雇佣的克劳琛,怎么可能允许他在大赛之前“临阵脱逃”呢? 中国足协和巴特基辛根的合作,可以认为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一次“错爱”,因为双方都有可以互相利用之处。中国足协能在尽可能少花钱乃至不花钱的基础上,在欧洲建立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平台,而巴特基辛根也可以获得名声和期待中的政绩。而已经脱离一线执教生涯数年的克劳琛则在巴特基辛根这个平台上找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和空间,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成为巴特基辛根“乱象”的受害者。 国青队在到达德国之初就为没有良好的饮食和住宿条件而发愁,队只有五个公用浴室,连训练后洗澡都有问题;比如说吃饭每顿只有两个菜;比如说力量房是给敬老院用的器具。这些直到谢亚龙访德之后才得到逐步的解决,而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中国队在德国期间虽然进行了11场热身比赛,但除了几场国际比赛之外,一些场次的比赛对手水平参差不齐。巴特基辛根方面没有提供足够的足球设施,中国队训练的场地不平直接导致了赛前两名队员意外受伤。所有的这些不尽如人意,再加上思乡之情,让国青队从上到下形成了对巴特基辛根方面的一种排斥力量。在国青队当中,克劳琛是巴特基辛根乃至德国方面最直接的代表。他实际上成为了中国队这种不满情绪的一个发泄口子,而谢亚龙在访问德国期间表态则让克劳琛彻底坐到了火山口上。由此这般,才产生了所谓克劳琛被“妖魔化”的形象。 在此期间,外界盛传中方特别是领队冯剑明和克劳琛的矛盾,而冯剑明对此的解释非常坦诚:“我和他绝对没有私怨,但我也不回避工作矛盾。我曾经和霍顿、米卢等多名外教共事,但也没出现过类似事情。”冯剑明告诉记者,作为球队领队和队委会主任,他只是尽了自己的工作职责,把中方认为的问题,包括生活、训练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形成书面稿,转交给德方和克劳琛。由此而见,在“妖魔化”克劳琛的前期,巴特基辛根乱象是直接原因,而部分媒体的恶炒更如同火上加油,导致了读者所见的妖魔化。 在世青赛前后,“克劳琛”三个字在中国媒体上被翻来覆去地煎炸烹炒,让读者尝够了这个64岁德国老头的酸甜苦辣,所谓“倒克”、“保克”两派也在媒体上此起彼伏,异常热闹,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妖魔化”克劳琛的概念。由于身处国外,对国内媒体当时的语境不甚了解,因此我并不全盘知晓“妖魔化”的概念,但是我想,如果确实达到了“妖魔化”克劳琛这个概念和程度的话,那么就究竟是谁妖魔化了克劳琛?如果没有达到妖魔化的程度,那么提出“妖魔化”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妖魔化呢? 但是此时,克劳琛和中方教练在具体的训练和比赛指挥上确实有不少分歧之处。6月5日前后,杨一民的抵达给事情赋予了转机。杨一民在公开确立克劳琛业务权威的基础上,也特别要求中德双方教练要互相理解、沟通和支持,比如中方教练组要根据克劳琛部署的原则向球员进行细化,比如作为主教练的克劳琛要主动和中方教练、球员沟通谈心,不能仍然扮演欧洲主教练的“甩手掌柜”角色。由此,中德双方的两股力量才更加紧密和谐地运转在一起。 针对比赛指挥期间,教练席和替补席上发生的某些细节情况。说实话,作为我们身处看台的文字记者,是无法现场了解情况的。事实上,我也相信,即便是较近距离的摄影记者也很难窥得全貌。但从事后采访的情况来看,我的理解是:克劳琛抓住了机会,体现出了他在宏观战术和策略上所拥有的丰富经验,中方教练组则在很多细节问题给他进行了“补位”,双方互相帮助之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但是同样的,成绩掩盖不了球队的问题。 我必须要重申几个很有代表性的细节。中德比赛结束之后,在球队最后的晚餐上,足协副主席谢亚龙、杨一民在讲话中都代表中方向主教练克劳琛和德中足球促进会给予了非常大的感谢,克劳琛在最后感言中也用“奥斯卡获奖者”的方式,感谢了他能感谢的所有人,几乎一个都没有少。 其他细节来自媒体。一个是中德比赛结束之后两天,我通过网络看到据说是《世界报》赛后采访克劳琛,克劳琛说了一句非常经典和网络的话:“谁能看透中国人的灵魂!”还有一个是针对董方卓问题,他对中国媒体的表达相对温和,至多是“他要用曼联球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据说对德国媒体则态度非常强硬地表示“要给弗格森打电话,董永远进不了我所执教的球队!” 很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起德国老头埃曼特·克劳琛的时候,我最清晰的记忆就是在中德比赛结束之后,他从体育馆混合区到球队宾馆,几乎一直在接受媒体采访,把大致同样意思的话,翻来覆去地做车轱轳状地表达。他脸色红润、语气略显激动,操一口非常简洁有效的英语,几乎和每一个有一定记忆的记者主动打着招呼。那一刻,他仿佛离我们很近,但又离我们很远。 作者 :本报记者 顾晨(来源:东方体育日报)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