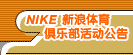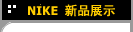| 《亚洲神射手罗兴梁》第一章:静不下来的童年 |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2年12月23日13:11 新浪体育 | ||
|
新浪体育讯 沿着苗栗市区内最大的中山路往火车站的方向直走,遇至丰年街右转后,约莫五分钟不到的车程,往左手边方向看过去,可以看到一块白底红字的木板招牌,上头的字是用朱丹红的油漆所画写而成,斑驳的字迹依旧可以清楚地读到店家的名字:和泰木材行。 那是我的老家;是我快乐童年的集散地;是我遭遇困难的避风港;更是我在外多年, 和现在都市小孩大不相同,住在富有浓厚客家村传统的我,可能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那种“庄脚囝仔”,没有都市孩子家中必备的电视游乐器,也鲜少看到高楼矗立、五光十色的都市街景,取而代之的是自己动手做的竹筒水枪,以及能让我们这群野孩子快意追逐的田边小道。少了都市孩童得面对的补习与课业压力,我很庆幸自己不用面对那些沉重的负担,可以专心地砌筑我的快乐童年,而这也是我的篮球梦之外,最令人回味与窝心的孩子梦。 最宠我的两个女人 在家中排行老幺的我,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家里的人开口闭口都叫我小弟,就算我已经三十多岁,他们还是没有改过口。 父母对我们三个孩子尽量一视同仁,不会特别偏袒谁。但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爸妈还是会对家中最“细汉”的我多了一点疼惜。妈妈更是特别照顾我,可能是小时候比较喜欢缠着妈妈的关系,再加上我国中毕业后就北上念书,看到自己最小的孩子,得在这幺小的年纪就出去打拼,心中的不舍与心疼不在话下。 其实到北部生活,吃住都有人照顾,人长高了,体重也相对增加。只是每次一回家,母亲开口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你为何变这幺瘦?一定是在外头吃不好。” 所以每次要从台北回苗栗家时,家人就看到妈妈在厨房里忙进忙出,不用说也知道,一定又是小弟要回来了。妈妈忙着烹煮我最爱吃的红烧牛腩、客家小炒、焢肉……等,都是我在北部生活时,光是想就会流口水的家乡菜。 纵使我的嘴巴已被食物塞得鼓鼓的,快吃不下去了,母亲总会念着说:“怎么吃这么少?”她总认为每一道菜是给出门在外的我,唯一进补与补偿的机会。为了不错过这种“双补齐下”,不让母亲失望,就算已经吃得很撑,我也会努力将菜肴一扫而空,而这似乎也扫除母亲的内疚与不安。姐姐每次看到,都会酸溜溜地说:“阿母又给小弟准备好料。”那时我总会不服气地与她拌嘴,说她爱计较。然而,我比谁都清楚,姐姐对于我这个出外的小弟,还是相当挂念的。 姐姐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摊开报纸找体育版,看看我昨天的比赛有没有刊登出来,或是与我相关的报导及评论,眼尖的她就像“剪刀手爱德华”似的,一看到罗兴梁三个字,就反射性地将报纸开了个天窗,把剪下来的资料,分别归类好,一点一滴地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数据库……在我结婚成家前,许多生活上的琐事,像是缴电话费或信用卡费,也都是姐姐主动帮我处理。我有时会觉得,家里好象有两个姐姐,又像是两个妈妈为我解决生活上的疑难杂症。 直到姐姐结婚生子,生活较为忙碌,我的数据库就再也没更新。现在翻着她之前用心帮我剪存下的每一篇报导,详细记载着我这一路的篮球历程,内心有说不出的感激。 另类家人“小白” 不过,在家里我可不只有“被宠”的份,还有个家伙会不时向我“邀宠”。 这位非灵长类的家人,它全身雪白,在客厅还有自己的专属座位,名字是很多养狗的人都会取的菜市仔名:小白。 这头白毛红鼻的狗,当初会成为家中的一分子,就是要它担当起守卫家门,看紧家中木材的重责大任。从国小开始,它已经为我们罗家守了十三年的门,和我们之间的那种亲近感,早已脱离上下主从的关系。 晚上睡觉时,小白会很自动地跟我上楼去,在我高中北上念书之前,我们都还是睡在一起。它庞大的身躯和我挤在一张小小的床上,虽然连翻个身都会撞到它,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安全感。所以高中一开始在异乡睡觉时,少了小白跟我凑热闹,我竟然还会认床。 小白的凶悍是我们那里出了名的,除了家人以外,面对其他人,它可是不会口下留情。有一次,隔壁卖鱼的伯伯,要过来跟家里借铁锤,妈妈在厨房里头忙,就叫他自己到柜子拿。才一下子,在二楼看故事书的我突然听到一阵凄惨的哀嚎声以及小白生气时的低吼。下楼一探,小白的利牙好像吸盘一样,粘在那位伯伯的大腿上,让他动弹不得,冷汗直流。 妈妈和我赶紧又是打又是骂的,才让小白松口。这时卖鱼伯伯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一步也走不动。尽管爸妈费了很大的工夫跟人家赔不是,也得到伯伯的谅解,但从此之后,就没看过他进入我们家门一步。 明基新浪狮队的队友黄春雄笑说:“它可能因为被阉了,所以心态不平衡,才会这幺凶。”其实我倒是蛮赞同春雄的说法,这种因自卑而引起的不满,可想而知。很多事情从心理层面去探索,有时要比科学解释来得简单、有趣。 每次从台北回到家里,门还没开,就可以听到它在门内又跳又叫的,看到它高兴的模样,就觉得相当开心。人家都说:狗养三天,三年不忘。我觉得我和小白的感情,就算过了三十年也不会改变,只是它能活这么久就好了…… 那时我已经在宏国甲组打业余篮球,而小白也已经是十三岁的高龄老狗。有天早上姐姐打电话给我,说小白过世了,死因是心脏衰竭。挂下电话,一想到再也没有谁会跟我争床位,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当天练球也是无精打釆,纵使当时我已经成年,却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不舍。平常就算输了球,我也很可以将心态调整好,迎接下个挑战,队友和教练都称赞我EQ控制得很好,没想到这时候什么Q都派不上场了,剎那间,我像是从一位成年人,蜕变成失去心爱宠物的单纯孩子…… 屁股长虫的小孩 如果说小时候,罗家三位小孩哪个最让父母,还有师长伤脑筋的?我想所有的票源可能会如同排山倒海般地涌向家中的老幺,也就是我身上来。现在只要他们回忆起过往,一提到我,总是先大笑,然后用一种“拿他没辄”式的摇头,简单的几个表情、动作,就可以体会出小时候我在他们心目中是何等的好动、顽皮。 或许就像老一辈的人所说的:“这小孩是屁股长虫啊!”要我静下来,实在是相当难以忍受的一件事。 记得还是在念幼儿园的时候,有次父母不在家,哥哥姐姐还没放学,我一个人闲来无聊,就跑到父亲用来载木板的三轮车上,在上头蹦蹦跳跳地玩了起来。当时只顾着玩,根本没注意到什么叫安全,结果一个不小心,跌了个跤,头就撞到三轮车的把手,马上破了个洞,血流不止。 一开始并没有很痛的感觉,右手按住头上的伤口,心中不知如何是好。有趣的是,那时还在考虑要继续玩下去,还是坐在门口等爸妈回来,想了一下,还是选择后者好了。结果父母一回到家里,在门口看到一个满头是血的孩子,吓了一大跳,母亲几乎都快昏倒了,二话不说,马上把我抱进去,用家里的云南白药帮我擦拭伤口。我觉得很奇怪,平常要是犯错,就会被立刻修理,这次父母竟然没有打我,可能是怕我头部受伤,再打下去可能会脑震荡,所以就放我一马,而这块疤现在还清楚地烙在我头上。还有一次,趁爸爸不在的时候,偷偷跑去玩锯木材的机器,其实我老早以前就想玩玩看,只是爸爸都镇守在那边,不许我越雷池一步。但越得不到的东西就愈想得到,我只好故作不在意的样子,寻找最好的下手时机。好不容易等他出门,自己打开那早就注意到的开关,待马达一激活,就开始拿木材来切割。没想到打开开关的时候,衣服不小心被机器马达的皮带给卷进去,不一会功夫,右手手指就被皮带绽出一个洞。还好皮带是橡胶软皮,所以只是轻微的皮肉伤,否则现在大家看到罗兴梁投球,可能是用左手。 爸爸看了直摇头,骂我说:“是你和我吃饭工具过不去?还是它们看你不顺眼?”那时在想,可能我不适合吃这行饭吧。 不过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每年过年的大年初一早上,我一定会完成的例行公事——摔进臭水沟。 大年初一摔成泥猴 小时候过年是相当具有年味的,大年初一的早上,客厅里总会摆满平常较少吃到的零食、饮料。亲朋好友都会过来家里拜年、热闹一番。几个穿着新衣服的小朋友在领完红包,达成目的之后,一开始假装乖巧的模样,早就不翼而飞,那时候哥哥总会登高一呼,带着我们这群小萝卜头,出去外头闯荡、溜达。 出门时,我和堂哥、表哥,各自骑着儿时最拉风的跑车、三轮车。一群人好比飚车族似的,浩浩荡荡地往外头出发。当时我们骑车的目的地是位在我家附近的台肥厂,那里除了有空旷的工地让我们玩耍外,重要的是在通往目的地的路程中,由于都是田边小径,路旁全是菜园,增加骑车的困难度,但相对的也增添许多驾驶乐趣。我常幻想我们这一群像是探险队,路程愈是艰困,愈能激发斗志,不到目的地,绝不罢休。 我总是跟在他们后头,一方面因为我的年纪最小,再来心想跟着他们后面骑,如果前面路况不好而造成“翻车”事故的话,在后头的我至少还可在后面看好戏。心里愈是这样盘算着,就愈是觉得好玩,骑车时迎面而来的风,更让我显得惬意无比。 经过一小段路途的跋涉,终于快到台肥厂了。这时冲在最前头的哥哥,发起了冲锋前进的口号,口令一下,人类最原始的竞赛本能被激发出来,心中的斗志已被点燃,大家立刻铆足了劲,红着眼、咬着牙,没命似的踩着脚踏板,使出百米冲刺的力量向前冲,那种六亲不认、奋力夺金的脸孔,对小小年纪的我有着相当大的震撼。 我的年纪虽然是最小的,但要我无条件向这些堂哥、表哥投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能!为什么我不能?”这种不服输的想法竟在此刻埋下种子,一直到现在,遇到困难阻碍时,我还是用这句话反问自己。我立刻站起身来,好像赛马的马师在冲刺阶段时一样,不停加快我脚踏板的回转速度。一下子,和他们的距离拉近了,离他们不到一个车身的距离。这样下去,甚至还有可能会超过他们,我已经开始想象超过他们时,他们那种惊讶又佩服的神情。 正当我陶醉在臆想胜利时,眼前的地平线开始扭曲了起来,整个景象好似坏掉的录像带一样,破碎而不完整,接着眼前一片黑,整个人呈倒头栽的姿势着地。 隐约听到堂哥在上面喊着:“小弟好像跌到水沟里去了!”我勉强抬头往上看,在亮光处有几个人拉长颈子往我这边瞧着,背着光看不出他们是偷笑,还是担心的表情!哥哥把我给拉了出来,活像只跌到泥坑的小猴子。等全身站定后,我终于看到堂哥、表哥的表情了,原来是在偷笑! 事情还没完,回家路上,表哥与堂哥安慰我:“今天是大年初一,习俗说大人不能打小孩,放心啦!一定没事。”但是妈妈见到我这副德性,气得直发抖,我想堂哥、表哥根本是在糊弄我。就这样,我成了家族中唯一大年初一就被修理的小孩。 妈妈打完之后,到了中午吃饭时,她夹起我最爱吃的鸡头放到我碗里,要我快点吃。母亲的这种教育方式,着实影响我教导孩子的观念,不管再怎么疼,孩子该教的时候,一定得表现出来,不一定要用打的,但至少要他们知道:“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往后两、三年,我还是犯了相同的错误,掉进同一个水沟,不要说堂哥、表哥他们,就连我都不相信会犯下这种相同的错误。但小孩的世界里,就是会一直碰到这种怪事,谁也无法解释。 或许,我的运动神经就是在一阵阵的追逐嬉闹中活络起来。就是这种定不住的好动基因,为我在各项运动中,打下厚实的基石。 生命中的第一颗球 很少有运动选手能像日本足球漫画里的大空翼一样,一开始就选定足球作为他运动的唯一选择。即便是篮球巨星麦可·乔丹,一开始也是跟着大家打棒球,后来才转进篮球路。这种误打误撞的情形在体育界屡见不鲜,我也不例外,一开始接触的,并非现在握在手中的红色球,而是体积较为瘦小的白球——排球。 由于哥哥国小时就是排球校队,常常看他在学校练习,渐渐耳濡目染,起了点兴趣,进而向哥哥讨教了几招。那时候只要是和运动神经扯上线的项目,我都可以吸收得很快,哥哥看我学得颇有心得,每次练球时,都会顺道拉我过去观摩。 其实哥哥是我从小到大的护身符,在他面前,我永远是那个爱哭、爱跟班的“小弟”。每回跟哥哥出去玩,弄得脏兮兮回家,第一个被砍头的一定是他,等他被教训完了之后,轮到我时,父母差不多也消气了。然而,哥哥并没有为此吃醋而私底下欺负我,相反的,每次出去玩耍,总是细心地注意我有没有紧紧跟在他的身后,或是注意我有没有受伤。就算长大后打进甲组及职篮,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关心我,几乎每场比赛都有他的身影与声音,只要在场上,好像可以听到他的加油吶喊声:“小弟!给他冲啊!”。这份兄弟间的情谊,从未因我离开苗栗而间断过。 当初打排球,除了想跟哥哥玩在一起外,就是顺便消耗小孩子体内那股永不耗尽的体力,根本就没想过能靠它打出什么名堂。然而在往后的日子里,虽然再也没有继续接触排球,这项与我无缘的运动,却为我敲开日后职业运动生涯的大道。 大约在国小四年级,有次照样跟着哥哥依样画葫芦,在旁边揣摩着杀球动作。当时哥哥的排球教练,也刚好是我的级任导师,平常就知道我是个相当好动的小孩,加上看我在旁边学得有模有样,看起来挺有运动天分,于是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排球校队?我心想,放学后可以用正当理由留下来打球,对一个爱玩的小学生来说,简直比钻石还吸引人。于是我二话不说,头就很用力的点了下去,就这么一点,点出了运动火苗。 直到今天,我还在想当初给老师的答案如果是摇头而非点头,我或许就错过通往职业篮球的道路。这种机缘可能一辈子就只有这幺一次,我很高兴并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好好老师,魔鬼教练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小学老师当中,我对他有种很特别的印象。过去担任小学的班主任可说是能文能武,从国文、数学,到音乐、体育,一手包办。也就因为如此,几乎整天都逃不脱班主任的的魔掌。要是遇到那种连学生放个屁都会歇斯底里的严格老师,那么上课时,最好保持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专心上课,不然一个巴掌随时就会轰了过来。而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好好先生,在老师在当中算是异类。 幸好我遇到这位脾气还算“温驯”的班主任,很少打、骂学生,否则像我这种上课还会不时转过头和朋友聊天的刺眼家伙,老早就被其他老师给轰到九霄云外了。 但是,在球场上的他,立刻摇身一变,成了魔鬼教练。只要你在球场上出了点差错,一个不注意,老师手中的排球就像躲避球一样K了过来。因此每次练球时,每个同学莫不把自己的神经强化到最大值。 也正是如此,我和一般同学的行为模式大不相同。别人上课是胆战心惊,我则是嘻嘻哈哈;但是当他们下课得到解放时,我的人间炼狱方才开始…… 不同运动,相同领悟 一开始加入团队生活,多少有点不适应,况且跟其他队友也不熟,感觉上和大家格格不入,练球时出奇的安静,一度让老师和哥哥担心,认为我可能不喜欢排球。但时间一久,与队友之间更加了解,蛰伏已久的好动性格马上苏醒过来,刚开始的不适应,也随之消失无迹。 排球跟篮球的类似之处,就是身材高的人较为吃香。因为不管是进攻杀球,或是防守拦网,只要身材够高,就能给对方较大的压迫感。没想到第一个接触到的运动,就因为我的身高不够高而没占到便宜。但也因为如此,国小时候的我就了解到,先天上的不足,一定得用后天的努力来弥补。 别人长得比我高,我就跳得比他高;杀球力道比不上人家,救球一样可以开启胜利的契机……。打篮球时遇到比我高出一个头的人,就用速度及假动作甩开他。或许老天没有判给我两米的高大体形,却在运动细胞与不服输的心态上补了回来。 不高!没关系,我全身的协调性与时间差的掌握,比其它队友来得好,教练也注意到这一点,为我设计了A式快攻的打法。这是所有扣球中,速度最快的一种,当对方还来不及判断我们的攻势为何时,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跃起扣杀得分。这种战术,身高不是绝对优势,良好的运动神经却可以成为相对优势。 特别面对防守拦网球员都比我高大时,这是对当时才一米六多的我,最有利取分的方式。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很快成为排球队上少数身材不高,却已担当起得分主力的球员。 升上国中以后,由于大伦国中是以篮球为发展重点的学校,所以国小的排球校队班底,也全队转移到篮球校队,那时也是我和排球说再见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打排球的契机,引领我进入运动大门,也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运动上小有天分。虽然排球的打法、战术,以及规则等,都和篮球大不相同,但两项运动所担负的使命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得靠团队力量,攻破敌阵,赢得胜利。 就像篮球的助攻一样,没人传球给你,拿什么去投篮呢?一样的道理,排球也需要有人将球二传给你,然后杀球得分。那时我就深刻的体认到,球队的胜利,靠的是团体合作,个人锋芒毕露的表现,不一定能带领球队迈向胜利的康庄大道。 小学毕业当暑期童工 尽管排球是我运动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童年生活中最刻骨难忘的回忆,却是一个月不到的童工生活。 对许多人来说,小学毕业代表暑期结束后,男生得理平头,女生得剪西瓜皮,笨笨地面对下一阶段的求学。而我却在这最后的暑期得到生命中第一份短暂又难得的工作经验。 和大多数的家庭一样,在苗栗这个都市化发展较为缓慢的地方,大家不是务农,就是做些小本生意,这种生活形态至今没有太大的改变,小时候家里做木材行的小本生意,主要就是卖些三合板、门还有模板……等。有时放学回家,看到家里的人正在为出货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自己闲在一旁挺不是滋味,常常跟着爸爸或哥哥,拿着铁锤,俨然一副木工小学徒似的,学钉模板。藉由这种方式为家里尽一份绵薄之力,对当时的我来说,是相当有成就感的。 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当大家抓紧小学生活无忧无虑的尾巴,狠狠的玩最后一次时,我的小大人心态又来了,那时觉得,既然之前都可以在家帮忙做事,现在更可以到外头工作,挣钱贴补家用。 于是我瞒着父母,跑到陶瓷工厂当童工,待在闷热的工厂里,跟师傅学陶土、拉坯。事实上,如果不把它当成是工作看待的话,我倒是认为这种创作还挺好玩的,靠着自己的一双手,任意塑造出我想要的形状与外观,完成作品时,还颇有造物主的快感。 那时在陶瓷工厂工作,难免搞得灰头土脸的,照理来说应该很容易被爸妈发现,不过因为小时候顽皮的不良纪录,他们并不以为意。直到有一天下班回家,爸妈竟然发现了,那时我整个心都凉了半截,不敢正眼直视他们。 没想到爸爸只淡淡的说了一句:“明天不要去了。”看到他们舍不得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在生气,生气自己没能让自己的孩子跟其它孩子一样享受暑假生活。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父母那种无言的愧疚,对我来说却是最沉、最重的责骂。
|
| 首页 ● 天气预报 ● 新闻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
|
|
|
|
| | ||||||||||||||||||||||||||||||
| ||||||||||||||||||||||||||||||
| ||||||||||||||||||||||||||||||
| ||||||||||||||||||||||||||||||
行业信息高速路!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2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