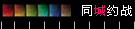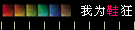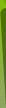这是属于他的幸福生活!和怎么都不愿意、甚至从来不曾跟队到训练基地参加春训的科萨相比,福拉多更愿意融入这样的生活,蒲江是他的,那些孩子、猫、狗、鸡鸭、土房都是他的……
记者比福拉多晚到蒲江基地几天,因为是老朋友了,福拉多一听说记者来了,马上赶到球队宿舍的大堂等着和记者见面。坐了两个多小时飞机一个多小时大巴十分钟人力三轮
(蒲江基地的出租车是清一色的奥拓,数量不多,等半天也不见一辆,只好坐人力三轮车)赶来的记者,到了基地大门之后,急急忙忙地往里跑,刚好遇到了助理教练石磊。“这么着急干什么?” 石磊一挥手指向大门的方向,那里福拉多正从大门外往里走,一边走还一边喊:“真的是你啊,刚才我看到你从三轮车里下来,我还以为是基地里来要签名儿的小姑娘呢!”
基地大厅里很冷,福拉多特意找了一个靠里面的桌子坐下。可能是觉得戴着帽子不太礼貌,他摘了下来,但摘了没有一会儿,又戴上了。“对不起,我有偏头痛,着凉了就会头疼得睡不着觉。”看见记者盯着他的帽子笑,福拉多从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个独立包装的巧克力威化,望着记者的伙伴不好意思地笑了。“不好意思,不知道是两个人,只有一块糖。”等在门口,还准备了糖,让记者很有些感动。“他肯定是个好父亲!”记者的伙伴点着头赞叹。福拉多马上好奇地看着记者,等记者把这句话翻译给他之后,他马上骄傲了:“当然了!我有两个女儿呢!”“中国人有句话,说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记者笑着告诉他。“棉袄?”在费了不少功夫理清了这个词的含义之后,福拉多忍不住感叹:“我有两件棉袄啊,好幸福!”让记者忍俊不禁。看着记者津津有味地吃着威化,福拉多忍不住问:“你和父母住在一起吗?我指的是一个城市?”“不是,他们在东北,我在北京。”福拉多皱了皱眉头。“你多长时间回家一次,去看你的父母。”“一年一次,有时候还回不去。”参加工作五年以来,记者只在家里过了两个春节。“你不觉得害臊吗?”福拉多说话的口气忽然一下子生硬起来。“没有办法,因为工作太忙,那个时候总是有采访任务,今年也是。”福拉多的表情不知怎么让记者平常说来非常理直气壮的理由变得底气不足起来。 “我也是搞足球的,我当然知道这行有多忙。但是我希望你记住,到任何时候,都不能以忙为借口而忽视了父母的感受,你要先做个好孩子,然后才是好记者。没有你的父母,哪有你的今天?”福拉多开始训人了,和刚刚给记者巧克力的那个他判若两人。看着他一脸严肃的样子,记者赶紧闭上嘴巴不吃了。这个时候,很多球员下来买东西,和记者打招呼,总算解了围。
一顶德尔惠的帽子、阿迪的外套、美津浓的裤子,一双不知什么牌子的球鞋、背着的双手、手里还总是拎着装着杂物的塑料袋儿,这就是出现在蒲江基地里的福拉多的形象速写。如果不是身边还有队员在跑、足球在飞,你会以为这是一个胡乱追赶“运动时尚”的本地老大爷,穿着从儿子身上淘汰下来的衣服,逛菜市场,时不时的东张西望像是在看蔬菜价钱,又像在考虑回家做什么晚饭。
记者怎么也想不通,那个记者认识的,从首都机场到大连周水子机场一直亲自用手拎着西装的福拉多,和现在这个穿着滑稽的福拉多哪个更真实。北京那边足协三令五申要打击派系呢,蒲江基地里的福拉多还是不懂得“避嫌”,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一直混穿着实德和冠城两家俱乐部的衣服在训练场上走来走去。到基地附近散步的时候他顶多会换个帽子,黑色的礼帽儿和运动服配到一起后,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偷地雷的”。
最后还是实德队的人看不下去了。紧急从大连征调了几套上个赛季的队服给了福拉多,这才帮他凑齐了一身阿迪装备。衣服整齐了,但帽子还是要戴着。有时候记者问福拉多,“你的黑帽子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么爱不释手?”“没有!”福拉多的回答像他的表情一样简单,保暖,冷风吹多了他会头痛。年轻人都是要风度不要温度,但是福拉多正相反,要温度不要风度。实德当然会给他提供帽子,也是阿迪的,但这顶绒线帽福拉多只戴了一次就不肯戴了,因为很多队员也戴着同样的帽子,他“不甘心”就这样轻易地被小伙子们给比下去,虽然他戴帽子的样子格外俏皮好玩,但总想与众不同的他还是把实德“官方指定用帽”给打进了冷宫,他宁愿自己到街上去买一顶,反正这个不大的地方他都转遍了,找商店是小儿科。虽然基地附近很偏僻找不到大的运动品牌,但是身为主教练,福拉多还是买了个中国的名牌儿产品戴上了。在蒲江市中心的商业区里,满大街都是“德尔惠”的广告牌,福拉多认为这肯定是个大牌子,就顺手买了下来。自从买了德尔惠之后,福拉多简直有些爱不释手,训练的时候几乎都戴着它。
福拉多买了一张中国地图,放在房间的茶几上,没事儿就戴着花镜在上面找啊看啊,完全一派老汉要进城的样子。他找大连的位置,找北京、找蒲江,找广州,拿手来回比画量距离。“广州是不是比蒲江大,那里肯定能买到我想要的DV。最近我新发现了一款DV,太经济实惠了,如果有的话我想买一个。”一天下午训练之前,福拉多请记者到他的房间跟他和日尔科以及翻译柴老师一起喝茶的时候,趴在地图前面突然来了一句。“欧洲的DV都是日本产的,很贵。没想到中国有这么便宜的,还不到三百美元。”福拉多一副很心动的样子。大家都想知道是什么品牌的摄像机能这么便宜,福拉多说他没有记住名字,因为电视里的广告都是拿中文做的,但是他经常能够看到,于是打开电视让对家看。结果广告真来了,记者一看,是各台都在轰炸式播放的“**拍”,里面既没有说用什么带子,也没有说拍摄时间的长短等等。很难吸引一个中国孩子、中国人看到了通常都会转台的这样一个产品,福拉多却信以为真,他一边儿看一边说:“你看拍得效果多好,跟普通的日本数码没什么区别,这不比那个便宜多了。”日尔科听福拉多这么一说,也开始头脑发热起来,跟福拉多说:“要不我们一起买,说不定人家公司还能给我们打折呢!”福拉多连连点头。让记者和翻译老柴都目瞪口呆。
福拉多买了一个新手机,但是却经常不接电话,因为他找不到打开铃声的按键,只能放在振动上。在房间里还好,但是在外面溜达的时候放在口袋里就总听不见,他让日尔科和翻译柴老师以及队医们帮他忙活了一大圈儿,都没找到铃声的开关,因为纯英文的操作界面,有的看不懂,看懂的也找不到振动改铃声的菜单。还是福拉多脑筋转得快,他建议把英文菜单改成中文的,调好了再改回去,可是大家找来找去都找不到语言转换栏儿,只有英文操作界面。“不可能啊,你看这里还有中国字呢!”福拉多把手机功能键按了几下,出现了几条手机里的中文广告信息,有的信息还是繁体字。记者马上想起来在香港手机市场上有不少改版的欧洲手机,能够接收中文短信,但是发短信只能是字母。看样子福拉多是买了一个水货手机,所以操作起来才如此别扭。
福拉多看样子是上当受骗了,他还把自己买的手机当成是眼下最时尚的手机款式,至少跟他原来的那个绿色荧光灯的屏幕比起来,白光的屏幕让他看得比以前清楚多了。找不到铃声他也不肯回去找人家评理,“算了,反正也不贵,顶多放到裤子口袋里跟身体近一些,这样就不会错过电话了。”福拉多乐呵呵地说。
这还不算搞笑,福拉多做的最好玩的事情是,在蒲江他理了一次发。“您剪头发了?在这里?”“是啊,就在旁边的那家理发店剪的!”“多少钱,不会太贵吧!”“这个……这个……”福拉多死活不肯说出价钱来。后来记者特意到那家理发店问了一下,普通的男士头剪一个多少钱,老板特别热情地说:“三块!”
什么事儿他都管,不管是不是他的管辖范围之内的。队员们吃饭的事情他也管,球队通常都是自助餐,爱吃什么拿什么,规矩多的教练,愿意让队员排队,不让带手机接电话什么的,福拉多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条,必须按桌打饭。他把队员的桌子分成几号儿,轮流第一个上去打饭。比如说今天是胡兆军他们桌先打,第二天就是阎嵩先打了,第三天就是季铭义……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提高大家的打饭速度,看着那么多队友眼睛在盯着自己不好意思挑来挑去;可是也有不好的地方,有时候遇到自己喜欢吃的,但是偏偏是别的桌先打,等自己过去的时候东西可能就快没了。但这样的情况肯定不会只发生在同一桌儿身上,这样做,就是避免好吃的都让个别人吃了,一哄而上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太顾及队友,最终福拉多的做法还是得到了认可,因为他每天也是跟着教练组成一桌儿加入到排队的行列当中去。
再就是他监督记者们看训练。在蒲江基地采访的记者一共也就四五个,往场边儿一站特别明显。“你今天怎么迟到了?”“怎么只看了半个小时就走了?”“结束后也不跟我打招呼就跑掉了,我还到处找你呢!”“你的闪光灯怎么只到11号(阎嵩)那里闪啊?”“你偷懒了,下午怎么没来?”每天训练结束后,福拉多都要挑剔一下记者的工作。
自从实德队到了蒲江之后,只出过一次太阳,就是在他们出发到广州的前两天。其余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小雨不断,所以,福拉多的训练场地偶尔会根据天气情况做出一些小调整。10块草皮,福拉多说不定到哪儿训练,开始几天摸不着规律的记者总是要在找球队身上花费一些时间,这样一来总是要比训练开始的时间晚个十分钟八分钟的。记者跟福拉多解释迟到的原因后,福拉多并不接受:“你要是知道自己不能在第一时间找到球队,就该提前一些时间到我们宿舍门口等着,那样你就不用到处乱转了。”在蒲江基地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福拉多替《足球》报的领导很好地监督了记者的工作,除了生病一次和三四次迟到以外,剩下的都是全勤。
与其他塞黑教练不同,福拉多并不喜欢喝咖啡,基地附近有很多茶楼,福拉多喜欢靠窗的座位。在离开蒲江前两天的晚上,记者和福拉多、塞维奇、日尔科一起喝茶,见到福拉多品茶的样子,塞维奇一直在笑,在记者的追问下,塞维奇终于讲了福拉多喝茶的趣事。原来在福拉多的房间喝茶,主人总是会自己亲自刷杯子,“你知道福拉多刷茶杯的第一步是什么吗?”塞维奇问,“嗯?放水?”记者不解地回答。“不知道了吧,刷茶杯的第一步就是把茶叶吃了。这是他的方法!”塞维奇指着福拉多哈哈大笑。福拉多也不辩解,后来真的拿手抓起了杯子里的茶叶放到嘴里嚼了起来。
隔壁桌是一群年轻人打牌,图拔是个牌迷,于是记者也问福拉多,是不是愿意用打牌来消磨时光。福拉多说他不喜欢玩儿牌,一个是觉得有损主教练的威仪,第二是对赌钱反感,而没有任何赏罚的玩儿牌毫无刺激,他更不喜欢。可嘴上说不喜欢的他总是盯着邻桌儿,“他们拿的牌好像跟欧洲的一样,是52张吗?”“他们怎么整个晚上都不说话,不无聊吗?”“这里允许公开玩儿扑克吗?在塞黑是禁止在公共场合打牌的,除非是赌钱!”怎么看都觉得他好像极爱打牌。
“难道你除了散步喝茶,就没有别的爱好了吗?”记者问福拉多。“他还有很多爱好,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日尔科抢着说。“他网球打得可好了,他小女儿是职业网球运动员,他总给女儿当陪练,还拿了不少业余网球手的奖呢。他还给女儿建了两个自己的专用球场,一个红土的和一个塑胶的。”福拉多在一旁不好意思地低着头笑,嘴里还说着:“一般,没他说得那么好!”塞维奇接着说:“后来他总是拿到业余冠军,主办方都不敢邀请他了,因为他一去,一些人就会积极性大减,因为他去了别人就知道冠军没戏了。”两人这么一唱一和,福拉多的脸都红了,红红的脸配上那个新头型,实在怎么看都不像网球大师。
全新推出中超联赛数据库 中超元年全面详尽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