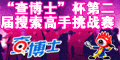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 甲A《城市笔记》之成都--李承鹏:暧昧 不只在夜晚 |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3年12月17日09:31 《足球》报 | |
|
慕容雪村不是成都人,他写的是烟花三月的扬州,或欲望横流的芭堤垭。 一个个湿湿的夜,一片片棉花糖式的天空,一条条暖昧莫测的街道,每个人都是心不在蔫地走路,心不在蔫地泡吧,心不在蔫地堵车,心不在蔫地排下“一四七”的“宽叫”,但心有灵犀猛地和上一把麻将牌。 成都的定位就是没有人能把这座2300年的城市准确定位,就像没有人能搞明白成都人哪有这么多时间、金钱消费人生,上帝偏爱成都——却不给它观点。 在翟迪说的“来历不明的夜”,或我说的“暖昧不清的天空”里;在“空瓶子”主唱沙哑的声线,或欧阳巧舌如簧的说唱上,在“仁和春天”高昂的Shopping,或染房街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采购中;在外地人喜欢的“皇城老妈”和本地人习惯的“粑子火锅”……每个人每天都在干两件事情:玩,和想着下一步怎么玩。 把人生兑作啤酒中的泡沫,把理想兑作芝华士中的绿茶,把追求延长至南延线两延线外的九尺生抠鹅肠……我把梦撕了一页,不知明天该怎么给。至于观点,让流沙河,余杰或魏明伦去说,让《新周刊》或慕容雪村去叙述,成都人用李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方式去生活享乐,哪用一丝半招套路。 爱一个人,送他去成都;恨一个人,送他去成都。天堂建在地狱之上,成都建在天堂之上——已经在天堂之上了,何必再长翅膀,所以在成都呆惯的人感觉湿润如母亲的子宫,何必远走高飞。 “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红万妆”,韦庄《怨王孙》怨的是生活如此多娇。 在古老青石板上碾过的司马相如高头驷马的车轱辘声,在青羊宫灯会上流动的是轻舞歌女的眼波如丝,在锦江剧场响起的是李伯清东拉西扯式的川味评书声。 如果这时你以为成都是个销魂蚀骨的温柔之乡,便会突然杀出一彪人马。有长衫裹头的“袍客”,有腰揣利矛的“哥老会”,有单枪匹马千死赵尔丰的尹昌衡,有在科甲巷要冒死从法场劫出石达开的铁衫党……还有魏群,一个为朋友身中17刀痛死都不打麻药的“魏大侠”——玉林小区的青色石路上,至今淌着挥发的“侠气”。 你无法给魏群定位,无法给“袍哥”定位,无法给这座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定位——全世界,只有成都的“肯德基”才低下高昂的头,给每位顾客涂配“辣椒包”。 生活在舌头上,生活在酒瓶中,生活在砸金花、斗地主、“机麻”的轮回中。夜一页一页暖昧不清地翻将过去,马麦罗打死也不想回巴西老家,“龟儿子,这儿巴适得很”,他会用最纯正的成都话述说人生的最后归宿。 在接受所有生活方式之后,成都人却不接受徐明的足球方式,球场的人慢慢稀少了,还抵不上一次“空瓶子”夜场的酒客。 只有一个数字可以告慰:四川足球在甲A10年中居然可以排到官方统计总分第5。这比《新周刊》的“第四城”更让人实惠受用。 但明天的四川足球会如何?谁也不知道,这么一个逐渐从纯良怀旧走向功利浮躁的城市,并没有盼来当年其中所说的“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条口子,让印度洋暖流直贯而入”的灿烂天空。 每天出门,天空都那么暖昧,不只在夜晚。(李承鹏)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