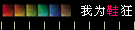梦剧场演绎曼彻斯特历史 伟大曼联骨子里刻着工业精神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12月17日15:25 《足球》报 |
|
英超城市笔记No.3站曼彻斯特[下]下一站利兹 那是一处独霸一方的建筑。从丁斯盖特商业区向西步行15分钟,远远就可以看见全英容量最大的“梦剧场”老特拉福德。由于地处昔日的工业区,球场周围基本上全是建筑密度不高的低矮厂房、仓库和新式办公大楼,屹立其中的“梦剧场”显得格外耀眼。这和座落在拥挤居民区的安菲尔德和海布利大为不同,也是老特拉福德能一再扩容的原因。 几经翻修,今天的老特拉福德无论在外貌还是内涵上都已跻身顶级现代化球场行列,球场正门覆盖整面看台的浅绿色玻璃甚至可以让你一窥俱乐部办公室的内幕。 每到比赛日,老特拉福德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万千球迷,而俱乐部商店门前巴斯比爵士的塑像也总是欢迎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大工业“制造”了曼彻斯特,工业精神也“制造”了曼联俱乐部。在崇尚整体的曼彻斯特人面前,局部或者个人从来都无足轻重。 时至今日,曼联俱乐部本身就已成为了一项巨大的足球工业。依靠着这座足球机器赚钱的不仅仅是红魔的股东们,还有制造出曼联的曼彻斯特居民———如果没有曼联,这座城市的旅游业将出现巨大的萎缩。 闲情之城 曼彻斯特,古称曼古尼亚(Mancunia),至今当地人仍然很喜欢被叫做Mancunian。公元1301年古罗马人开始在这里建立城市的时候,永远也不会想到500年后,Mancunian用一场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以机器、铁路为代表的大工业时代,成就了曼彻斯特的辉煌,也造就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气质。 对于中国旅游者来说,大概很少会涉足工业烙印深刻的曼彻斯特———这座靠棉花起家的城市似乎从来就没洗净过身上的煤灰,它大而无当,复杂却缺乏特色……论昔日的历史、今日的热闹,似乎总不如伦敦甚至是爱丁堡。但对于球迷来说,“曼彻斯特制造”的曼联却像一块巨大的磁铁。 其实在曼彻斯特,最好看的也不是风景,而是这里的人,这里的生活态度。在过去20年里,远离了蒸汽和汗水的曼彻斯特不仅仅只为足球呐喊,还跨进了一个打扮时髦、到处聚会寻欢的青春年代,甚至发展出一种“早餐也要喝香槟”的闲情逸致,以及注重享乐到几近轻浮的人生态度。 和拥有“慕尼黑空难”的曼联一样,曼彻斯特也有过沉重的历史,不仅仅是1996年爱尔兰共和军在市中心制造的那起爆炸案。1819年,政府与近6万被剥夺了公民权的“暴民”在市政厅前的圣彼得广场发生冲突,骑兵冲击人群造成11人死亡、400人受伤,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彼铁卢事件”(Peterloo),意指穷人的滑铁卢(Waterloo)。“彼铁卢事件”导致了1832年的改革法案和宪章运动,改革主义者也于同年在这里创办了《曼彻斯特卫报》,就是今天《卫报》(TheGuardian)的前身。 曼联球星享受平凡 国王街(KingStreet)10号,一条距离安黛尔购物中心仅50米的普通街道,一座外表上了年纪室内却装修一新的普通建筑。5年前,这里成为阿玛尼(Ar-mani)在曼彻斯特乃至整个英格兰西北地区惟一一家专卖店。 也正是这家专卖店让阿玛尼和贝克汉姆走在了一起。在转会皇马之前,前曼联7号几乎隔三差五就会开着他的“悍马”来此一游:车子就停在专卖店门口,那时贝克汉姆的身边还没有黑衣保镖,他只身一人钻进店铺,没有个把小时根本不会出来。然后,走出大门时,贝克汉姆手上总是拎着数不清的大包小包。两年多之后,英格兰队长钟爱的Armani时装便成为了英格兰国家队指定礼服新供应商。 出没于国王街10号的当然不只是贝克汉姆一个,在他的影响下,曼联群星几乎都是这里的常客,但这条街道却依然相当僻静,曼彻斯特的居民只有在球场才把他们当作明星,以至于流传在坊间的一种说法是,贝克汉姆之所以选择离开,原因之一就是曼彻斯特人对待明星的态度。 在曼彻斯特,球星更是与普通居民没有分别。这里的人们热爱足球,也非常支持当地的球队,但却可以自如地在足球与私人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日常生活中的球星在他们的眼中不过是些凡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即使受到全英宠爱有加的贝克汉姆,当初在曼彻斯特也没有得到什么特殊待遇,结果只好不时找点借口跟辣妹结伴南下伦敦。或许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找到真正明星的感觉。 与贝克汉姆“难耐寂寞”不同,留在曼联的众多球星却似乎很受用平凡的生活。从国王街出发向西穿过两个街口,横在你面前的一条繁华大街就是著名的丁斯盖特(Deansgate),临街的那家LivingRoom餐馆则是范尼、吉格斯、内维尔兄弟这些人以及当地各界名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事实上这里供应的欧洲风格菜式价格并非想象中那么离谱,中等收入的市民完全有能力和明星们一起消费。 沿着丁斯盖特继续向北,也就是百多米的距离就到了街道的尽头,那里高耸着一座全玻璃结构的崭新建筑物———丁斯盖特1号(DeansgateNo.1)。这座大楼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整个楼体的外形酷似一片扇形的蛋糕,也是2002年英联邦运动会期间城市改造的杰作,现如今已经是曼彻斯特最昂贵的住宅大楼。由于新家的装修要到明年年初才能完工,在那之前,刚买下一座旧农场用作住宅的加里·内维尔就住在这座大楼里。 至于丁斯盖特1号的位置,其实就在每天都人潮汹涌的安黛尔购物中心的一角,而楼下几步开外,专卖国际名牌的HarveyNichols百货大楼赫然在目。一年多前里奥·费迪南德因为搬家忘记接受药检而与曼城好友贝尔科维奇结伴跑到市中心采购,光顾的正是这家时尚名店。此外,当年吉格斯初为人父第一次被记者拍到抱着小女儿上街的照片,地点也是这里。继续向北,很快你可以走进一座外表并不是很炫的大楼,但那里却是一个集酒吧、餐馆、电影院、游戏厅等为一体的娱乐休闲中心。值得一提的是位于1楼的Nando's墨西哥烤鸡店,这家餐馆的现烤美食成名已久,我也曾经慕名前往品尝过一回,但没想到今年6月英格兰国家队在曼彻斯特进行欧洲杯备战热身赛期间,埃里克森还领着全体球员在那里饱餐过一顿。只有在曼彻斯特这样的平民足球天堂,英格兰群星们才能够如此安静地在市区和普通居民一起共进晚餐。 工业革命传播足球 为什么曼彻斯特人会如此淡薄地对待球星?或许还得从大工业时代说起。 如果没有两个世纪前的那场工业革命,曼彻斯特不仅不会有全英第二大城市的地位,也不可能拥有今天的繁荣和活力。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参观一下坐落在近郊的“城堡地城市遗产(Castlefield)”,那里是英国第一座城市文化古迹,随处可以看到锈迹斑斑的铁桥、破败的厂房和仓库,就像是一座“工业历史博物馆”。 尽管世界上第一部蒸汽火车并非诞生于此,但曼彻斯特却铺设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轨,目的是连通西面的港口利物浦,将这里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世界各地。引发纺织技术革命的“珍妮纺织机”同样是曼彻斯特的杰作,在那个生产力还极其有限的年代,最早实现了大规模生产的曼彻斯特也最先完成了对世界纺织品市场的垄断,而“曼彻斯特制造”随后也成为了全球的时尚。 然而属于“曼彻斯特制造”的还远不仅仅只有棉布,就在曼彻斯特影响着两个世纪前全球经济生活的同时,来自英国的水手以及技术工人同样把现代足球运动传播到世界各地,经过100多年的传承发展,才有了今天世界第一运动的特殊地位。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没有这座在蒸汽中成长起来的城市,现代足球的历史很可能要改写。另一方面,作为足球运动最早期的参与者和观赏者,大工业时代的产业工人们很自然将整体放在了第一位。这种思想一直贯穿着整个曼彻斯特发展的历史,也贯穿着曼彻斯特联队发展的历史。 即使曼联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俱乐部,其市场价值预估接近8亿英镑,但翻开俱乐部厚厚的历史纪录,第一页便清晰地记载着:1878年,一群爱好足球的火车车厢制造工人组成了一支球队,并将其命名为纽顿·希斯。1902年,也就是球队开始征战甲级联赛以来的第10个年头,一名当地的工厂老板出资500英镑买下整支球队,并且宣布,从此以后这家俱乐部的名字叫做曼联。 时至今日,虽然过去遍布球场四周的厂房和仓库已逐渐被现代化办公大楼和购物中心所取代,但在1930年铺设、连接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世界上第一条铁轨上,仍然保留着老特拉福德这一站,从月台到球场的入口仅仅是几级台阶的距离。每到比赛日,这里与市中心的牛津街车站都会开通专列运送球迷,以这样的方式来怀念先辈的记忆历史,自然再合适不过。 工业精神制造曼联 源于曼彻斯特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改变了足球运动。同样弗格森的“工业化”手段也深刻改变了曼联。 在弗格森的办公室里,一幅巨大的画像几乎占据了半面墙的位置,那是1932年在纽约洛克菲勒大厦建造期间创作的摄影作品《Menonagirder》(梁上众生,也有人译为《曼哈顿的午餐时间》)。对于出生在苏格兰高文船坞工人家庭的弗格森来说,选中这幅画的理由显然不是画里11名建筑工人悬坐半空的惊险场景,而是照片中所蕴涵的深刻意味。距离地面数百英尺的一根钢梁上,工人们却能从容地享受片刻休息,需要的不仅是过人的胆量,更是工人阶级彼此之间无间的友爱和信任。通过这幅照片,弗格森不仅希望自己的球员像工人们一样团结,更无意间提醒人们,无论曼联再怎么成功,它崇尚整体的根本策略绝对不会改变。于是,无论老特拉福德人来人往,阵容几经换代,爵爷一生信奉的“工业足球”思想却是代代传承:球队结构拥有严密的组织,球员各司其职但同时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战术上更是追求工业化的简练高效。 高举“工业足球”大旗的曼联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造就了曼彻斯特足球圈一个独特的现象。在这里,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是凌驾于俱乐部之上的明星,而是整架足球机器中一个普通的零件。这样的思想同样深深地影响着一代曼联球迷,甚至整座城市对待球星的态度也和其他地方大相径庭。也许正是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和足球运动本身的真谛不谋而合,在弗格森执教期间,红魔拿下了8座英超桂冠、5座足总杯、1座联赛杯以及1座欧洲冠军杯,成就了曼联王朝的伟业。 上个月和里昂的冠军杯比赛之后,弗格森爵士完成了带领曼联比赛1000场的纪录,成就了一段不朽的传奇。但就算已年满62岁的爵爷,骨子里面却一直保持着一名工人后代的特性:粗暴、刚愎、坚忍、强调集体。 股份制有利有弊 在红魔精神的面前,个人的“平凡”并不意味着平庸,或者贫困。最新公布的英格兰足球富豪榜上,前10位中竟然有4人的身份是曼联股东。尽管这再次证明这家豪门俱乐部雄厚的经济基础,但同时也突显了另一种尴尬:源自普罗大众的曼联却越来越成为少数有钱人的玩物,国际化的市场策略以及抬高球票价格等一系列商业举措也正在改变着俱乐部原有的形象。反映在现实生活当中,曼彻斯特人以拥有曼联而骄傲自豪,但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在曼联身上感受纯粹的足球乐趣,更多人早已习惯于一打开当天的《曼彻斯特晚报》,第一件事不再是查阅前一天赛事的比分版,而是曼联股价究竟是涨是跌。不过,俱乐部的股份制性质至少对球迷的参与意识是一种促进。和许多同样号称“上市”的英格兰俱乐部不同,曼联股份很早以前就实现了真正的公开买卖,而不是由某一位巨富(通常也是俱乐部主席)占据着最大比例的股份而一手遮天。 在曼联,即使你是一个持股份额还不及万分之一的小股东,你同样有权利也有机会对俱乐部的建设发展发表意见。因此,在出发点更为单纯的“曼联独立球迷协会”(MUISA)之外,“曼联股东联合会”(MUSU)也是俱乐部的另一大骨干球迷组织,这在英格兰乃至世界足坛同样是独一无二的,何况这两大组织在旗帜如林的英格兰球迷圈里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正是这些拥有强烈主人翁意识的球迷,让收购红魔的企图一次次破产。最近两个月来,如果你有幸造访老特拉福德,就可以在巴斯比爵士路的入口见到那面著名的“非卖品”(NOTFORSALE)横幅。如果是比赛日那就更壮观了,激进的曼联球迷会高举横幅在赛前来一次示威大游行,从球场南面的特拉福德吧(TraffordBar)到北面的萨尔福德码头(SalfordQuay),有时候队伍可以聚集到上千人的规模,他们针对的对象就是美国佬格雷泽尔。 但也必须看到,也正是在股份制下,管理层在进行决策时处处受制,主教练也往往不能根据球队的需要而是必须按照财务报表来决定是否补充新血,俱乐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被迫放慢了脚步。在足球产业乃至全球经济“变天”的今天,曼联需要球迷坚持不懈地支持,也需要一个更灵活的管理体系。8月底引进鲁尼的过程中,曼联董事会总算走出了打破条框的第一步,尽管随后关于值不值得的争论一直在继续。 未来淘汰爵爷? 上世纪的最后10年,以电子科技为代表的后现代工业革命同样席卷到了曼彻斯特,电脑代替了蒸汽,厂房也一座接一座变成办公大楼。然而,就在这座城市已经随着电子音乐的明快节拍而摇摆起来的时候,这里的足球,却又一次落在人后。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阿森纳和切尔西的崛起中兴,英格兰足球势力的中心正在迅速朝南面的伦敦偏移。在那个更大的都市,有着更多可供俱乐部发展的资源,也有更为开放、更国际化的环境。 在俱乐部经营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上,曼联其实走在了所有英格兰俱乐部的前面,甚至远远超前于曼彻斯特的发展轨迹。这些还应该归功于曾经担任俱乐部CEO的肯扬,他的出现不仅让曼联俱乐部的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同样让英格兰足球俱乐部的经营模式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但就是这样一位足球经济领域的奇才,如今却在伦敦的斯坦福桥。 然而真正令曼联忧郁的却不是肯扬。在老特拉福德鞠躬尽瘁超过18年,弗格森以他的丰功伟绩已成为了这家俱乐部的图腾和象征———爵爷就是曼联,所以也才有两年前苏格兰人提出准备退休时,球队立刻便出现了动荡。可是任何一段历史都有画上句号的一天。至少在现在,曼联已经呈现出了极盛至衰的现象。回到“工业足球”的理论,如果弗格森是现在这座巨大“赚钱机器”的驾驭者,那下个优秀的驾驭者将是谁呢?一个巨大的难题,就如工业革命中寻找一位能推陈出新的伟大工程师一样艰难。 幸好在曼彻斯特,你依然可以欣喜地看到,人们并没有放弃先辈的传统———每个比赛日,无论曼联还是曼城的主场,总还是人满为患,如果不是早早预订,你根本别想搞到一张比赛的门票;面向青少年和业余级别球队的周日联赛(SundayLeague)也依然如火如荼,曼彻斯特人并没有因为拥有一支举世闻名的球队而放弃自娱自乐的权利。 事实上,这里的业余足球的水平之高,是很难想象的。当年贝克汉姆、内维尔兄弟们在跻身曼联后备培养体系以前,就是周日联赛中的常客。即使是今天,在爵爷的影响下,众多曼联现役球员也纷纷利用训练比赛的间歇接受教练培训,而实习的对象,往往就是一些纯粹凭爱好组成的青少年球队。正是这些与内维尔们操着同样口音的孩子,恰恰才是曼彻斯特足球的希望所在。 城市名人堂[曼联] 麦特·巴斯比(MattBusby,1909-1994)巴斯比爵士的传奇之处不仅在于第一次率领一支英格兰球队夺取象征着欧洲最高荣誉的冠军杯,也不是他在曼联主教练岗位上指教23年的历史,而是经历了1958年那场著名的“慕尼黑空难”后,仍然可以重新回到赛场,并在悲剧发生整整10年后完成曼联的重生。那场空难中,8名曼联主力球员罹难,但在1968年5月的温布利,一支以博比·查尔顿、贝斯特等领衔的全新“童子军”4比1战胜葡萄牙豪门本菲卡,巴斯比也终于可以带着梦寐以求的桂冠结束自己的执教生涯,也于当年得到了女王的授勋。退休之后,巴斯比也曾先后担任过俱乐部的董事和主席,为了纪念这位为老特拉福德奉献毕生的“曼联先生”(Mr.ManchesterUnited),1993年,横穿球场正门的沃维克北路被改名叫做“巴斯比爵士大道”(SirMattBusbyWay)。 阿历克斯·弗格森(AlexFerguson,1941-)正如不久前完成千场带队纪录时爵士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当初从阿特金森手上接过曼联帅位时,没有人会想象到,苏格兰人一待超过18年,而且以大大小小17座冠军奖杯成为英格兰足球史上最成功的教练。虽然在位时间尚不及前辈巴斯比爵士,但是弗格森对俱乐部的贡献、尤其是对俱乐部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他成为曼联的象征和代名词。“爵爷就是曼联”,现任俱乐部CEO吉尔道出了所有曼联人的心声。 博比·查尔顿(BobbyCharlton,1937-) 1958年2月8日,当时仅仅21岁的查尔顿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两天前他的8名队友则永远地倒在了慕尼黑机场。作为空难的一名幸存者,红魔曼联“死去重生、永不言败”的精神在博比·查尔顿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不仅帮助球队在1968年取得那场著名的冠军杯胜利,此前两年就以队长身份率领英格兰在本土举行的世界杯上一举夺魁。1973年查尔顿结束其球员生涯的时候,他已经为曼联效力了752场比赛,打进247球,而他在国家队49个进球的纪录至今无人企及。和他的恩师巴斯比爵士一样,查尔顿并没有就此停止为老特拉福德效力,1984年,查尔顿结束了自己短暂的执教生涯,担任起俱乐部的一名董事,直到今天。 乔治·贝斯特(GeorgeBest,1946-) 1961年,只有15岁的乔治·贝斯特刚刚加盟曼联时,他的身份只是一名球童。然而短短7年之后,这名来自北爱尔兰的前锋便以28个进球成为球队的头号射手,还在当年冠军杯决赛中射进一球,帮助红魔一圆欧洲称王的梦想。随后的4个赛季中,他在361场联赛中打进136球,垄断得分王称号的同时还创下了单场进球6个的俱乐部纪录。然而生性玩劣毁了贝斯特的球员前途,在1972年仅仅26岁的他突然宣布退役,此后数次试图返回赛场,但最后均以失败告终。 (本版撰稿/摄影:王康宁) |
|
|
|||||
|
|
|
| 新 闻 查 询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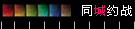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