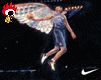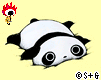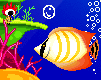| 基恩自传连载(2):我的“处子秀”在安菲尔德上演 |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08月08日05:01 新浪体育 | |||||||||
|
《我不是恶人--基恩自传》 [爱尔兰]罗伊-基恩/伊蒙-邓菲 著 张军 黄红跃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咨询电话-0731-5711666-80922;直销热线-0731-5713359 殷先生 第二章 回森林队报到参加赛季前的集训时,我为在家的庆祝付出了代价:第一个星期如同地狱。头几天根本没看见球,只是跑步、耐力训练,然后是健身,中间穿插着旨在锻炼快速恢复能力的训练。幸运的是我和加里·鲍维尔,雷蒙德·伯恩合住的房子就在城市运动场边上(从我的卧室窗户可以看见足球场),所以几乎每天晚上都能挣扎着回到家中。职业球员都怕赛季前的训练,哪怕身体最好的在头几天都感到痛苦。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体力和耐力都不错,现在终于明白了职业和半职业比赛之间的天壤之别。我还看到并非只有我才有这种感觉。过了头几天,球来了。我挺过了最艰难的体力磨砺阶段,现在开始享受自我了。 我根据周围的形势,努力想找出在这里干下去所面临的挑战的实质。就在我加入前一个星期,森林队获得了小伍兹(联赛)杯。主力队里全是杰出的队员,斯图亚特·皮尔斯,德斯·沃克和斯蒂夫·霍奇都是现役英格兰国家队队员,奈杰尔·克劳夫也差不多在同样水平的边缘,享有代表的荣誉。皮尔斯显然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他刚参加世界杯决赛回来,在半决赛的一次关键的点球中他没有射进,但根据我好奇的目光的观察,这并没有降低他在城市球场上的声威。 在预备队中,和我训练的有斯蒂夫·斯顿、伊安·沃恩、阿奇的儿子斯科特·戈米尔,他们是非常出色的球员。菲利普·斯塔巴克也是很优秀的年轻队员,曾在主力队出过场。 利亚姆·奥凯恩带领主力队训练,阿奇·戈米尔负责我们。我们并非经常见到布莱恩·克劳夫,但是总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他那条金黄色的猎犬戴尔,时不时进入眼帘,表示克劳夫到了训练场。突然间每个人都像挂上了加速挡,只有我除外,因为我一直在竭尽全力。 我爱这个工作,如果这叫工作的话——5人组足球、练习赛,甚至健身训练我都喜欢,因为我知道这些是为我好,而且我也逐渐地适应了职业俱乐部的节奏,一天比一天感到强壮。 和我在家的情形比起来,这里简直就是天堂:那些不确定因素、永远漂泊的感觉、关于某某球探对我有兴趣的谣传、子虚乌有的试训、临时工、与拿救济金只差一步之遥的生存状态、一星期7天既要在漫步者踢球又要参加FAS训练课程的日子、躺在床上等待《邻居》(幻想着凯丽),还操心下5集什么时候上演等等——和那时的情形相比,现在可以说是太好了。我甚至在头几个星期全天训练那段时间,每天早上都有种陶醉的感觉。8月10日我过了19岁生日,第一次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生活。 在后备队的更衣室里,我快乐的天性与里面的气氛格格不入。一些队员表现出的态度让我感到惊讶,甚至震惊。他们什么都抱怨,比如主力队照相时没将他们也叫上等等。这对即将开始的赛季可不是个好兆头。也许是这样,去他妈的,你能做点什么!他们说阿奇·戈米尔是个老变态;布莱恩·克劳夫是个懒鬼;我们太辛苦了。赛季还没开始,这些人就说怪话,为失败找借口。我不太说话,但忍受着这一切,并发誓永远不成为哀怨者。这些人要是想想外面有多少孩子情愿献出右臂来换取他们现在的位置——在风和日丽的夏日里,坐在那里,拿着足球运动员的高薪——该多好! 这么一比较,我觉得自己晚加入职业队是好事。19岁的我已经踢了4年的球。至少看来如此。实际上,他们反过来也是对的。当我还在现实生活中学习如何对待失败、不顾一切地想获得一个机会成为他们中一员的时候,那些哀怨者和说怪话的人多半已经在他们15岁时就已经成为职业选手、在梦幻世界中生活了。对他们而言,作为森林队的职业球员是拿到了通向辉煌的车票;而进入主力队,幸福自然而然会自动随之而来。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而现在,生活并没兑现那些承诺。可是对一个来自梅费尔德饥肠辘辘的爱尔兰工薪阶层的青年,生活从来没给我任何承诺,所以我不觉得别人欠我什么——事实上,我的感觉正好相反。 当主力队出发去意大利参加赛季前的旅行时,我随21岁以下年龄队开赴荷兰参加一个季前联赛。我们的对手包括体育里斯本、巴塞罗那、埃因霍温和东道主俱乐部哈勒姆是我们的对手。第一场开门红,2比0轻松击败体育里斯本。我感到很舒心:葡萄牙人是讲究技术的球员,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体力因素在比赛中的作用。接着,我们以5比1重创埃因霍温,而我则射进了职业球员生涯中的第一粒入球。再后来就是哈勒姆以2比0打败了我们——作为东道主,他们没有自觉地遵守21岁以下的规则,而是让主力队球员上场与我们对抗。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已经踢进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巴塞罗那。他们抢先破了我们的大门。接下来就变成了一场风格的较量,结果巴塞罗那队在考验中败阵。我们一开始加快反击速度,他们就开始耍赖。他们越是这样我越发愤怒。巴塞罗那队的一些球员简直就是他妈的骗子,到处寻找犯规,目的就是想轻易取胜。尽管他们在比分上领先,但他们实际上已经举起了白旗。你可以感觉到,可以嗅到血腥味。我们的传球和拦截让他们受尽折磨;我们抢夺每个他们没有防守好的球,最终以令人舒心的3比1赢得比赛。 决赛与哈勒姆再次碰面。比分咬得很紧,菲利普·斯塔巴克靠一个点球将比分追平成1比1,进入了点球大战。我们每个人在面临严酷的考验时都牢记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决赛:英格兰在半决赛时罚点球不中战败,而让西德队捧走了冠军桂冠。虽然我这一球会定胜负,但我觉得我们不能步英格兰的后尘。我毫不怀疑作为一个森林队的队员我能通过第一次重大的考验。总而言之,我做到了。 和斯蒂夫·斯顿、伊安·沃恩、菲力普·斯塔巴克以及斯科特·戈米尔这样的优秀球员同场踢球是件很轻松的事,而且也容易得多,因为我不必踏遍场地上的每棵草来抢球——周围都是优秀球员,我就能更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跑到位,在对方点球区域寻找机会。 本赛季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在森林队预备队中占一席,因此哈勒姆锦标赛的战绩令人鼓舞。回家后,预备队的第一场赛前比赛是与一个非联赛队,萨顿·因·阿什费尔德。我被选为替补,坐在替补席上。这可有点令人失望,因为布莱恩·克劳夫在场,而且我太想给他留下深印象了。半场时我进了更衣室,要阿奇·戈米尔出去。 事后我才知道了他们的谈话。 克劳夫:“我想要你安排爱尔兰人试试。让你儿子斯科特(中场)下来。” 阿奇:“我安排他下半场上。” 下半场开始不久我看见克劳夫爬过边界墙朝着阿奇喊:“阿奇,让爱尔兰人上。”过了15分钟没有动静。我一直低着头。还剩下20分钟了,阿奇将斯各特换下,将我换上场。我感觉到自己是被勉强换上场,但是我要利用最后剩余的时间大大表现一番。 几天后,预备队出发与另一个本地的非联赛队,阿诺德镇进行比赛。队里的一些职业球员觉得这个队不如他们。这可不是他们生来具有的“梦想”。比赛前的更衣室里能够感到怨愤。这一次我首发上场而且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我了解他们:阿诺德镇队的球员结构和科卜漫步者队一样,既有一些态度好但能力平平的兼职球员,又有一些能力强技术好但脾气急躁的队员。对于他们全体队员,特别是态度正确的好球员,与诺丁汉森林队比赛是件大事。他们拼命都要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水平(如果命运没有捉弄他们的话,他们有可能全部穿上森林队的球衣)。 我清楚这种感觉。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漫步者踢球,迎战客队西布隆维奇阿尔比安。对他们而言,在这个被视为村镇的地方踢球,简直就像在公园里散步。而对我们,那简直就是世界杯决赛。我们全心身的投入,而且受到本地球迷的鼓舞,全力拼抢。那对他们已远不是友谊比赛了。 阿诺德镇队沉重打击了森林队。我们一眨眼就输了个3比1,丢尽了脸面。那个小场地里拥进了近千人,他们竭尽嘲弄调侃之能事。我深感屈辱,迁怒于队友,努力想用某种方法激发他们的斗志。这就是在预备队更衣室里该死的怪话所导致的结果。称自己是职业队,可是让阿诺德镇队吓得尿了裤子。这下子他们就像皇家马德里队一样拼抢并表现得趾高气扬了。 有几个真正的职业运动员明白了我的心思。我们开始竭力拦截和进攻。我踢进一个球,将比分扳成了3比2。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些人到底是真皇家马德里队呢还是他妈的阿诺德镇队。我又进了一球,顿时令观众闭了嘴。比赛结束时,我们算是赢得了一点自尊。 在森林队当职业球员的头几个星期证实了我早已明白的事理:这个世界里充满了虚张声势、欺诈和诡计;而在这里,那些只满足于带上职业球员臂章而技术不怎么样的人比比皆是。我需要证明自己是否名副其实。他们想跟随阿奇·戈米尔一比高低,而阿奇·戈米尔曾为苏格兰效力并获得过锦标赛奖牌和欧洲冠军杯;他们也想和俱乐部经理叫劲儿,可经理也不是好惹的,他曾为两个小俱乐部——森林和德比——赢得过两次冠军和两次欧洲杯。这难道是个笑话或是什么? 时间会证实我不是卫道士,但是早在足球生涯初期我就明白了:称自己为职业球员和像戈米尔、克劳夫和斯图亚特·皮尔斯那样通过努力赢得人们尊重的球员之间的差别。他们的标准是我努力的方向,而且我清楚自己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然而这条路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遥远。没有几天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周六,甲级赛季的第一场,森林队对QPR队,1比1主场打平。奈杰尔·詹姆森罚点球进了一个球。我是一个满腹计谋的看客。场上气氛很好,球场保养得有如地毯。这才是我经常想像的甲级足球。森林队对赛后结果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是当时的强队之一。 比赛结束后,我得知自己在与阿诺德镇比赛中的表现并没能让我在下周一晚上与罗特汉姆比赛中成为预备队员。我依然还是替补队员,因而十分沮丧。在比赛只剩下10分钟时我被派上场,没有任何时间组织一次进攻。赛后的晚上,我和其他预备队队员们一起到镇里喝酒,而且醉得不省人事。那时已是凌晨2点。 第二天一早,我在训练中露面。那天晚上主力队要在安菲尔德比赛。我一到市球场,还没有完全从昨天晚上的醉酒中清醒过来,罗尼·芬顿在更衣室里就找到我和菲利普·斯塔巴克:“你们两个去安菲尔德。”他说。“哦,带上鞋。”他添了一句。 好呀! 我暗想,费尔菲利普的简称好歹在主力队踢过几场球,是个有天分的小伙子,所以他去是有意义的。至于我,显然只是让我去体验一下,提提包和给管理员当下手什么的。后来证明我错了,事实是斯图亚特·皮尔斯、斯蒂夫·霍奇和特里·威尔森受伤了。 主力队是头一天晚上走的,所以我和费尔只能搭罗尼·芬顿的便车去。在去利物浦的路上,我们拐去德比接经理。布莱恩·克劳夫的房子很大。我上前按门铃。 “爱尔兰人,你好呀?” “很好,老板。” 他当时正在往外放空牛奶瓶,他夫人站在楼上。他从门里拿出一瓶差不多满的奶瓶子。 “来,爱尔兰人,喝了它。” 天哪,我可是很讨厌牛奶的! “我不爱喝牛奶,老板。” “喝了它” 别多嘴,罗伊,喝下去! “谢谢,老板。”说完我就一口喝了下去。 与此同时,克劳夫夫妇开始兴奋地交谈起来。她肯定喝得比我多。 “走吧,爱尔兰人。” “再见,克劳夫夫人,很高兴认识您。” 我们抵达主力队所住的旅馆,吃了赛前餐。我一直紧挨着费尔,因为这屋里我就只认识他。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 安菲尔德看起来很大。开球前一个小时,场上已经充满了跃跃欲试的气氛。利物浦队是英国足球的贵族,有伊安·拉什、彼德·比尔兹利、约翰·巴恩斯、雷·休顿和罗尼·威兰。他们都是国家队队员,加在一起更是无比强大。布莱恩·克劳夫喜欢的就是这种气势——其它球队早在看见通向球场的过道里的“这是安菲尔德队”标志时就已经被打败了。克劳夫在这里向安菲尔德的传奇发起了挑战,并将这个信息传达给他的球员。 为了让自己有点用,我主动帮管理员打开装备。 “爱尔兰人,你干吗?” “帮忙呀。”我回答。 “穿上7号球衣你要上场了。” “你说什么?” “你是来踢球的” 我惊呆了。 幸亏我没工夫过多考虑我的首次甲级赛。在安菲尔德与英国最好的球队对抗在45分钟的空间里,可以大做文章,比如向森林队久负盛名的主力队队员们做自我介绍,因为那时还没有谁知道“那个爱尔兰人”到底是谁! 在球场上热身时,我还在不停地回答着“小子,你叫什么来着”这个问题。 “罗伊。”我告诉他们。 他们真棒。传达给我的整体信息是:“祝你好运,孩子。” 奇怪的是我走出更衣室时很镇定。克劳夫很有胆识且聪明:他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判断,对已发生的事情也不退缩,没有给我任何压力。 虽然在那天晚上拉什和比尔兹利各进一球,利物浦以2比0轻松取胜,但我觉得自己表现不错。我记得自己在边线将球回传给斯蒂夫·迈克尔马洪,然后做了一个双过。确有其事吗?我问自己。回答是确有其事,干得不错。这么一来就觉得很舒服了。 安菲尔德所有观众都是很睿智的球迷,在他们面前比赛是一种享受。观众看比赛不带偏见,无论谁踢,只要踢出好球,同样得到喝彩,就连我表现出众时也得到了观众的欣赏。那天晚上在安菲尔德,我也体会到了爱国主义的局限。都柏林人罗尼·威兰用一次在高空争抢中的受伤欢迎他年轻的同胞——来自梅费尔德的罗伊xxx(他连我的名字都没记住)加入这次聚会;我还和雷·休顿来了一次毫不留情爱尔兰式的骨头相撞。 这是我运动生涯中仅有的几次输球后仍感到愉快的退场。我们竭尽全力了。如果在比赛开始时大家不知道我的名字,现在他们应该知道了。 赛后,我给爸爸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参加了与利物浦的比赛。就像我在几个小时前一样,他也非常吃惊。 “怎么样,儿子?”他问。 我答:“挺好啊。” 那确实是我当时的感觉。这次比赛除了证明我能够在最高水平比赛中有所表现外没有别的。没有人对我有太高的期望值,而下次我就得维护自己的声誉,同时也将承受人们更高期望值带来的压力了。这下我已有了第一次尝试,所以我的目标是要在主力队中争得长期的席位。 第二天上午,我在城市体育场的更衣室里见到布莱恩·克劳夫,他问我叫什么。“罗伊。”我回答。然后他脱了沾着泥土的鞋,因为他刚在球场上遛完他的狗戴尔。“罗伊,能把这个给我弄干净吗?”我愉快地从命。我明白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但我绝对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危险。 接下来的那个周六,在考文垂客场的比赛中,我保住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和对手打了个平局,但如果我在下半场能抓住机会传个好球什么的,我们是可以赢得比赛的。再下一周是我在主场第一场对南安普顿,我父母和几个舅舅赶来看比赛。我的一个朋友到东米德兰斯飞机场接他们,而我则去看少年队上午的比赛。阿奇·戈米尔看见我站在球场边上,非常生气。 “你在这里干吗?”他问。“今天下午你有一场重要的比赛。回家休息去。” ……(待续未完) |
|
|
|
|
|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