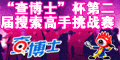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
“我的爱人啊,你美丽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掉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
1994年的秋天,我与我的朋友Angela坐在校园的梧桐树下,正午的阳光穿过被风掠得稀疏的枝桠,斑驳的光影落在我们身上,她纤长的手指抚过膝上杂志中的一幅主图,唇边衔着恬淡温暖的笑意,用悦耳的声音流畅地背诵着《雅歌》中的诗句,而图中那位名叫罗伯特.巴乔的男子正微晗着双目望向镜头,那眼眸幽蓝,辽远而渺茫,如印象中清澈晴朗的星空。
我小心翼翼地提出异议:“别被‘威武如展开旌
旗的军队’迷惑了,这几句诗似乎是新郎用来形容新娘的。”
“那有什么所谓。”她说:“他的美是超越年龄和性别的,甚至与容貌都关系不大,存在于灵魂和精神之间。”
这话听上去有追星族的盲目崇拜之嫌,但到如今,回头再看沧桑历尽后巴乔那倔强的身影,感慨的眼神,我承认我对她的观点其实一直深感赞同。
他的生命被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决赛分为两段,之前的意气风发,力挽狂澜,和之后的坚韧不屈,与逆境抗争,像一篇宏大乐章,万壑争流的激越之后是旋?微沤的余波激石。而最令人心折的是当年玫瑰碗决赛中的他,那场比赛乏善可陈,人们记住的惟他而已——当日他腿上裹着的硕大药包,那仿佛散发着浓郁咖啡香的飞扬的发辫,和最后射失点球后那天地化为零的沉重撑腰一低首。
1998年世界杯点球决战重现,他一脚中的了结心中隐痛,阿尔贝蒂尼和迪比亚吉奥却沿袭了他往日的悲剧,他没有责怪他们,比赛结束后,他拉起倒地无言的阿尔贝蒂尼拥着他离去,对手的胜利在他的宽容面前瞬间失色。而我们无法估量2002年特拉帕托尼将他摒弃于国家队外的决定给他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世界杯金杯是他不灭的理想,通往理想的大门被这个冷酷的决定轰然关上,他日益增长的年龄让他再看不到任何希望。
在他之前似乎从没有球星把缺憾演绎得如此完美。贝利曾说意大利人应把巴乔的进球画下来收藏进他们的博物馆,而他的足坛生涯何尝不是又一幅最具艺术美感的蓝色画卷,充满不可思议的空灵与令人扼腕的残缺。
听到他即将退役的消息我并不感到惊奇,仿佛早知一切会是如此,就像曾经给人荫凉的树叶会在秋冬时节悄无声息地淡然飘落。但我知道我会怀念他,他是一个我关注过,并影响过我的男子。我曾凭着无上的热情跟学西班牙语的室友学意大利语中也有的大舌音,只为能准确地唤出他的名字“Roberto”。从秋到冬,然后在某个春寒料峭的傍晚终于听见室友宣布我发音成功,于是我心满意足地捧着书去图书馆自习,一路如歌唱般一遍遍念着“Roberto”,其间有个黑褐色头发灰蓝眼睛的男子迎面走来,听见我唤的名字不禁微笑了,我猜他是意大利人,便也愉快而友好地对他微笑。
我想他离去之时一切也仍是美的,70年代女子依然恋恋的情怀与2004年新生的烟霞一起落在他肩上,他没戴有“球王”或“皇帝”的冠冕,但也没拖着他们的药物,他们的绯闻,他们的私生子的阴影,他行走的路途上遗下一道如月轨迹,未尝盈满,却甚皎洁。
只是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终于他要离去,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我们也无法等到他转回。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我在心底再次默念他的名字,不由又是一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