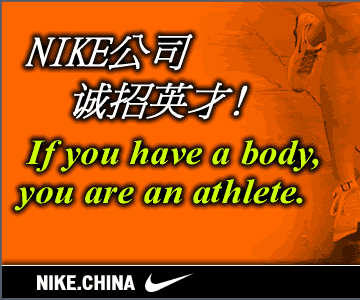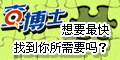| 张惠康:国门寂寞路边摊--唐全顺:最佳射手愁白头 |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3年11月14日11:03 竞赛画报 | |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上海滩,是冒险家们的乐园,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这里享受到冒险成功后的荣耀与幸福。上海滩,是成功者们纸醉金迷的天堂,但天堂里也会有人在成功过后,只剩下一道锈迹斑斑的光环。 -记者张平谊
岁月总是按部就班地把年轻改写成苍老,把活泼改写成迟钝,不经意间,一段繁华已演化成落寞,一段叱咤已风化成麻木。 一代国门寂寞路边摊 岁月如歌。张惠康的岁月,是悲歌。 这个上世纪80年代的亚洲最佳门将身手曾是那样矫健。在中国足球最耻辱的岁月里,他始终悲怆地独自把守着最后一道关隘。张惠康是1988年奥运会上那支被布拉特斥之为“最没有进取心”的中国队中惟一的勇士。若非他多次救险,鼎盛时期的联邦德国队绝不止攻进3个球,而中国队末战0比0逼平突尼斯队,获得可怜的1分,也同样依赖他的出色表现。一年后的新加坡,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决赛,最后一场中国对决卡塔尔,著名的“黑色三分钟”在张惠康手边上演,终场哨响,离实现最近的世界杯中国梦灰飞烟灭,只留下张惠康和队友们空洞迷茫的眼神。 谁也没有想到,这眼神竟然又出现在14年后张惠康的脸上。这次不再是因为竞技场上的遗憾,而是为了生活的重压。这个城市14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窗外车水马龙的喧嚣似乎与他无关。他依旧和父母一起住在从小住到大的蜗居,报纸上以前上海队里的后生们一个个开着SUV,憧憬着欧洲的假期。而当年球门线上一夫当关的猛将已经变成了一身赘肉的迟钝的中年人,被禁锢在上海西南角一个精神病康复中心的高墙大院里。在那里,张惠康就像《飞跃疯人院》中那个高大的酋长,总是对着天空发呆。 病情轻的时候,张惠康会接到几个朋友的邀请去踢场野球,反应虽然迟钝,但是基本功还在,几个动作还是很漂亮的。在普陀区建德花园的一所小学内,记者和张惠康曾经“同场竞技”,比赛后大家都围着他说话,分给他香烟抽。张惠康总是默默的抽着烟,不想说话,也不怎么喝水。一个朋友调侃问他怎么去香港守门时哭了?张惠康依然无语,他的脑子里在想其他东西,已经忘记了一秒钟前的问题。同样,他也不愿提及与傅玉斌之间的恩怨,对他来说,回忆和考虑问题都是极度耗费心力的。 “忧郁症引发的轻度精神疾病”,残酷的诊断让人心酸,但是谁又能体会这背后十数年的没落、自卑和艰难。1993年退役到现在,张惠康日子过得很清苦,现在除了每月到体委领取900多元的退休工资外,再没有别的收入。而900多元对于他这个病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张母说,她每月要去医院付张惠康600多元的住院费,“他连自己都养不活呵!”老人的声音中带着哽咽。 上海曹杨六村的人喜欢把张惠康唤作阿康,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记起他曾经是中国国家队的守门员,只是在买些杂货的时候与这位看摊儿的人进行几句匆匆的对话,再有就是聊几句天气怎么样之类无关痛痒的话题。阿康不喜欢人们再提足球,他曾苦笑着把国家队、上海队的1号球衣随手扔掉,小店里的时光好打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发福了,头发里多了几缕白发,背驼得挺厉害。没错,这就是那个曾经挡住许多强劲射门的身躯。 也不是没有人关心他的生活,市彩票中心照顾张惠康,让他卖足球彩票。小小的彩票亭设在马路边上,开始生意还可以。但是很快就被盗贼和不顾规定近在咫尺开设的新彩票亭给硬生生地挤垮。人情世故,这个从小就只知道侧扑愉悦的人恐怕是永远都学不会了。 八月份,上海市体育系统职工帮困基金成立,张惠康作为首批受捐助的对象接受了一万元的捐款。然而施舍能够换回青春吗?能够换回那一条条伤疤的愈合吗? 张惠康的身体状况除了他个人的内向性格外,与他1991年在比赛中一次严重的头部受伤也有着脱不了的干系。“那回我撞中门柱,感觉脑袋像被斧头劈裂似的,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医生告诉阿康,这是神经性脑震荡。为此他吃了整整10年药,直到现在。前职业时代缺失的医保机制和体育界淡漠的风险意识终于令一代门神犹如荒漠里的迷途者,越走越绝望,直到瘫倒在命运的脚下。 最佳射手愁白了头 当然,比身体崩溃更可怕的是心灵崩溃。在张惠康接受杯水车薪的捐助同时,当年的队友唐全顺则在上海东北角的一个看守所里度日如年。 今年5月8日,在一个叫“凤凰大酒店”的旅馆里,唐全顺因为开盘赌球被警方逮捕,很快被法院判处四个月的拘役。“脱毛的凤凰不如鸡”,想当年,作为甲级联赛最佳射手“三毛”是上海,乃至中国足坛响当当的人物。 然而,从1997年离开当时在甲B下游徘徊的浦东队到现在,唐全顺说他一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细究起来,他的人事关系应该在上海体育运动学院。“我曾经去那里人事处问过,有没有工作安排?那里人却让我辞职,说一次性可以给我几万块钱,还说鞠李谨(三毛队友,也曾入选过国家队)也办了辞职,拿了3万块。但是我不想辞职,人总要防老的。当时我心里想,我也是对上海足球做出贡献的,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后来我打电话给市少体校,问我能不能在那里给青少年队当教练?人家回答说,位置都满了。”体育的大门就此关上,可天才孟浪不羁的性格又让他无法安于一分安定的普通工作,他终于还是回到了足球的怀抱——以一种错误的方式。 九月,“三毛”出来了,要回家了。他先要去当时拘押他的派出所取回扣在那里的两部手机和一千多元现金。那一千多元钱,便是他的全部流动资金了。三毛退役后诸事不顺,开饭店赔了30万,过去积蓄的老本一点一点都磨光。做广告、做旅游,也没有挣到多少钱。现在位于上海普陀区宜川路上一套居住面积19平米的小居室,这便是他唯一的不动产了。三毛说一想到这,一想到将来,他便难受。他指着头上的一些白发说:“这都是想出来的,过去我从没有白头发。” 三毛说这话的时候,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有谁会注意这个失意的前球星呢?媒体的关注只是一时兴起,浪花平静后,谁会在乎一个唐全顺,一个张惠康。那些名字只是一个个符号,静静地在图书馆里被笼罩在灰尘下。 “三毛这个人就是太散漫。”唐全顺的恩师王后军这样骂着这个弟子,“社会上朋友实在太多,人嘛也讲义气要面子,前几年就听说在赌球,没想到……唉!”王后军还是对唐全顺有惋惜之情,但三毛以前的老队长王钢却没那么客气,“他这样的人,出来了还是出去混,混油掉的人怎么会走上正路。”王钢和以前的队友朱有宏、李中华、鲁妙生、秦强等都定期相约在同济踢球,但他们从来不去叫三毛。 无论是张惠康还是唐全顺,他们共同的感受是“在这个年代我们没用了”。这么多年,这个城市一直在场边品评那些球员,欣赏或唾骂着,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曾去探究过这些表演者的感受。他们中的某些人因为财富的关系,种种真实的不如意被掩饰了,而面对晚景凄凉的失败者,除了同情,我们似乎拿不出更多来帮助他们走出沼泽。 也许我们只能说生活中难免悲剧,但愿张惠康和唐全顺是这悲剧最后的殉难者。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