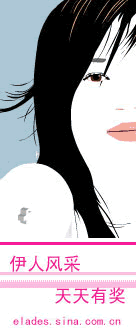|
69
飞机还停在沈阳桃仙机场的三号机位,乘客们陆续开始登机。
我的座位号是22排B号,宁殊是A号。22排是一个靠着安全门的位置,我本想让宁殊进到A座上去,这个位置靠着舷窗,看看风景很方便的,可后来我把两个大包放在行李架上后,
宁殊刚要从我身后去自己的座位,我轻轻一抹身,一屁股就坐在了A座。我的这个动作一点不生硬,我坐下了,宁殊只是瞥了我一眼,然后在坐在了临座上。
早晨是陈超开车送我们来机场的。沈阳到成都的航班是在早晨,我曾告诉陈超不要起早来送了,酒店下面的出租车多的是,可陈超早晨六点就敲响了我的房门。
在沈阳这么长时间了,陈超奉行的基本上是小商小贩的原则:无利不起早。他要找我,一定是有事情相求。在我临离开沈阳的时候,我觉得陈超有点忽发神经,也许他觉得有点内疚吧。他的那本论文集子,原计划半个月就能出来,可现在,许多人钱都交了,人也都要离开沈阳了,那本书的书稿竟然在出版社编辑手里,还没有交付到印刷厂。陈超的解释是,出版社当时和印刷厂的合同当时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出版社考虑到这本论文集印刷只有几百本,根本没有当回事,直到出版社想印刷厂发出最后通牒,双方才同意集子10月底一定出来。
陈超的车开得象老牛一样,从酒店到五里河他竟开了半个多小时。
早晨车流滚滚,可我也看到过欧阳在上下班高峰时开车的样子,他在车流里见缝插针,游刃有余。欧阳曾自豪地说,自己开车有点疱丁解牛的感觉。他说他开了五六年的车,城市在他的眼里不再是完整的了,它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街道组成的,他握着方向盘,让自己的车能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街道间,能及时避开红灯,警察和任何不守交通规则的行人,准确及时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地。
陈超开车时甚至很少说话,直到车到五里河体育场时,他回头对我们说:"再看一眼福地吧,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宁殊忘着窗外的五里河体育场,她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下来。
她最初落泪的频率很慢,当车开到浑河桥上,五里河体育场淹没在身后一群高楼之间时,她好象觉得沈阳真的要被这条郊外的河隔离了,她的泪水大滴大滴地落下来,还伴着抽泣。
"刘备妹妹,不要总这样,说不定还会有机会来呢。"我说。
宁殊也不看我,眼睛只是盯着窗外。出了城,早晨的阳光显现出强大的穿透力,她们把田野里的庄稼和房屋勾勒出辉煌的轮廓。我把手搭在宁殊的腿上,不时地轻轻拍两下,我是想安慰住她的泪水。这些日子,他的眼泪的确很多。
拐下机场高速公路,宁殊要开始从车窗里向南望着。那是绿岛的方向,在她的心目里,在绿岛下榻的那支神奇的球队,也许是沈阳这座城市不朽的唯一标识,除了球队,这座城市在它自己的政治地震中好象已经腐烂了。
在侯机厅里,宁殊看到的除了形形色色的乘客外,剩下的就是我这张没有一丝笑容的脸了。要回成都,我的确笑不出来。我失去宁殊,也要失去老婆,成都这座城市恍惚间与我好象没有了任何关系,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在沈阳找个工作,守侯在老爸老妈身边。
可是,惯性总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在情感与生活的惯性里,我还是很坚决的和宁殊登上回成都的航班。我俩是什么?只是两个乘客,两个曾经睡过觉后不想再睡了的乘客。
还是什么?
失去了情人身份,一夜间我和宁殊仿佛也是易燃易爆危险品,我们被命运从沈阳押送回成都,我们彼此小心谨慎,避免着磕碰。
飞机中午经停西安,起飞后不久就开始飞跃秦岭。
那年来成都读大学时,秦岭在我的车窗外是巍峨的山峰,陡峭的岩石,以及郁郁葱葱的树木。我喜欢列车一遍遍钻山洞的感觉,漆黑黑的山洞让车窗的玻璃变成了一面镜子,我看着自己那张消瘦的脸在玻璃里晃动着,那种颤动与轰鸣来自秦岭最深层的泥土之中,我感到自己和秦岭已经没有距离了,这种感觉让我有点幸福,因为以前的秦岭只是我地理课本上的山脉,我牢牢地铭记了它,但那时我连秦岭的一棵小草都不如,现在我却钻进秦岭的心脏。
现在,秦岭又变成一个名词,一个概念,因为一望无际的云层把它遮盖得结结实实。
宁殊靠在坐椅上,眼睛盯看着机舱里小荧屏上的电视广告。那是赵本山和范伟为沈阳一个房产商推销房子的广告。两个人眉开眼笑,机舱里许多人也看着他俩咧着大嘴,我弄不明白,这个年代人好象真是堕落了,两个大红大紫的农民,一人放一个屁,人们竟然能笑两三个小时。
我用胳膊碰了下宁殊。
"飞机过秦岭了,不到一个小时你就到家了。"
"你不也到家了嘛。"
"成都是你的家,不是我的家,我什么都没有了。"
宁殊听到我的话后,没有反应。我是暗示她,我到成都后马上就要和老婆办理离婚手续的。宁殊不会听不明白我的意思,可她没有任何态度。
我闻到一股脚的臭味。我低着头四处查看一下,发现臭气是从我前排的一个30来岁的小伙子脚上散发出来的。我用手捏着鼻子坚持一会儿,后来实在无法忍受了,我站起身来,拍拍前座小伙子的肩,很严肃地对他说:"兄弟,味道太大,把鞋请穿上好吧?"
这家伙看我一眼,"你是空中警察啊,什么都管?"
"你TMD把鞋穿上,行不!"
我的声音抬高八度。我这一声喊叫象按到什么开关似的,机舱前部的坐椅上许多人象电子狗一样,脑袋齐刷刷地转过来看着我。
一个满脸雀斑的空姐也过来了,她微笑着看着我。
"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你让他把鞋穿上就行了,他在污染环境。"
宁殊用一种不耐烦的眼光看着我,"那么大声喊什么呀?注意点影响啊。"
我瞪她一眼,没有理会她。我看到那个光脚的小伙子被我吼叫吓着了,他低下头,用手划拉着自己的鞋,没用一分钟就穿上了。
那个雀斑空姐微笑地站在小伙子身边,直到他把鞋穿好,她才离开,可是在转身的一刹那,我看到她竟然用手捂下自己的鼻子,她这一举动让我有点反感。
即使那小子把臭脚放到空姐的鼻子上,她也不能去捂自己的鼻子。这就象三陪小姐明知道客人有口臭,也不能拒绝客人的嘴巴一样,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我觉得。
几分钟后,我感到很失落的不再是臭脚和捂鼻子的空姐了,我对身边宁殊的麻木有点愤怒。我刚才和臭脚斗争的时候,她除了抢白我一句,大多数时间是靠在坐椅上,眼睛盯着小荧屏,拿出一副不愿意理我的样子。
"你没有闻到臭味儿?是不是鼻子出了问题?"我不冷不热问她一句。
"我看是你精神出问题了。"她说。
"精神出问题的话,昨晚就把你强奸了。"我把嘴放在她耳边,有些恶狠狠的语气。
"你的嘴比那个人脚还臭。"宁殊瞥了我一眼,接着看娱乐节目。
"我可没想和你吵架的。"我长吸一口气,"臭就臭吧,反正都回成都了。"
"莫名其妙!"宁殊说。
我也是觉得自己的最后一句话有点莫名其妙。我好象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了。
我从舷窗里看到厚厚的云层上空,是蔚蓝的大气层,那是一种深邃的忘不到边际的蓝色空间,那种蓝色冷艳得让我感到有一丝的卑微。我在云层的上面,我竟然不能超脱得象一朵几躲轻盈的云,我竟然计较着脚臭和一个女孩子对我的神态,我感到有点好笑。
还有那洁白的云层,她们平铺在离飞机几十米远的下方,她们团结得没有一丝缝隙,无边无际地蔓延着。这是天堂的棉花?是一种不容任何杂渍玷污的颜色。
秦岭就在云层的下面,还有村落,或者还有蒙蒙细雨;还有耕牛以及在田野里奔忙的人。这些仿佛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
"我看是你精神出问题了。"
我耳边又响起宁殊刚才的话。我用余光瞥一眼宁殊,她依旧用刚上飞机时那种姿势坐着。她拿出一副根本不想多看我一眼的样子。
我继续从舷窗里俯瞰着,整齐的天堂的棉花让我心惊肉跳,这完全是一种被白色感动的躁动,我眼睛忽然也盯上了我身边安全门那个红色的把柄。我有一种欲望,我想在云层上漫步,一个人轻轻地走在上边。
那红色把柄先向外一拉,再按箭头方向旋转一下,这架航班右侧的安全门就会洞开。这也是我云中漫步唯一途径层。我要去拽把柄的的欲望很强烈,我甚至身体向安全门方向靠了靠,我想大喊一声,告诉所有机舱里的人,也包括宁殊--我要去散步了!
但我的手始终没有动……
我在暗暗提醒着自己:自己的大脑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手。我的一个学医的朋友告诉过我,如果一个胆小的人走在漆黑的夜里,他忍受不了极度恐惧,突然疯狂奔跑并大叫起来,这个人的精神就彻底崩溃了。
我没有去拉把柄,我眼睛死死地盯着宁殊,我真希望她能为我去做这一切。她打开舱门后,我们一起走出去。
宁殊睡着了,竟然还伴着微微的鼾声。我看到她的鼻尖上有渗出来的点点汗珠。她有些热,我扬起手,把头顶的风孔稍微调大一点,又把风孔对准她肩膀的位置,我没让风直接去吹她的头,人在睡觉的时候,冷风不仅能吹得人头疼,也很容易把人吹的口斜眼歪,这是老妈告诉我的,我小的时候她就告诉我睡觉的时候,一定离风口远点。
飞机擦着云层不停地向南飞着……
我知道,这个秋天,我的家已经没了方向。
(全文完)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世界杯短信游戏多多:点球大战、足球经理、世界杯大富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