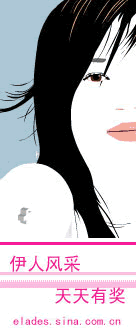|
67
国家队打完卡塔尔的第二天,大多哥们都要走了。
一大早,唐嘉和欧阳开车去大连玩了。我那该死的领导前两天已经告诉了唐嘉,让她乌兹别克的客场比赛就不跟了。球队出线了,报纸也没有什么卖点了。唐嘉听到这个消息乐
坏了,她告诉我要和欧阳去大连玩两天,然后再回成都。
10点钟爬起来后,我先到楼下送老林和关雷。关雷离开酒店的时候,给梅昕打电话,她手机没有开。我把梅昕家里的电话给他,关雷拨通后开始和她告别,老林也把电话接过来说了两句。我最后也对梅昕说,我今天要回家看老爸老妈,估计没有时间见面了。我说下次回沈阳一定到她家做客。梅昕最后叮嘱我回成都后一定要给她打电话,我满嘴承诺。
送走关雷和老林后,中午送迟兵。中午的时候,要走的记者特别多,一楼大堂里拎着大小包裹的几乎都是这帮人。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每个人堆里都站着一两个女孩子。她们有的眼泪汪汪的,有的牵着要走人的手轻声细语。在前台结帐的地方,武汉一个哥们拿着票据正仔细端详着,他身边的那个女孩子把手直接伸到他裤裆处,我最初吓了一跳,后来才发现那哥们的前门开着,女孩子是再帮他拉着拉链儿。
迟兵身边是一个瘦高个子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我只在比赛前一天见过一面,连名字都忘了叫啥。梅昕不再和他上床了,高颖远在俄罗斯演出,我让弟弟从他公司里面找一个容易上的女孩子推荐给迟兵。我只听弟弟说,这个女孩子是个朝鲜族人,挺开放的。两个人接上头后,迟兵表示相当满意。两个人只温存几天。迟兵要走了,他在大堂里搂着那个女孩子的腰,嘴放在她的耳朵上不知说着什么。
随着国家队主场比赛的结束,任何要离开沈阳这座城市的异乡人,都应该喜剧里一个角色,因为球队世界杯出线了,中国人意淫世界杯40多年了,现在终于在沈阳射精成功,每个和足球有关的人,都应该有种做爱后的喜悦。
可我不知道,足球出线和我这样的记者有多大关系。
我知道的是,我现在灵魂里空空荡荡。我能穿行在酒店的大堂里,完全是因为在沈阳这个秋天,我仅存的好象只是一点友谊。为了这些友谊,我踉跄在人群中,寻找着那些感伤的情怀,一个个送走朋友们。
迟兵的脑袋就差点钻进女孩子的怀里了。我在大堂里和哥们们打了好几圈儿招呼,转过头来,看到迟兵还在那里粘粘呼呼的。
朝鲜族女孩子温柔多情。提起这个民族的族女孩子,迟兵应该有深刻印象。三年前,当他和一大帮记者随球队到延吉比赛时,迟兵听当地人讲,离延吉几十里外的小城黄龙很开放,是男人的天堂。迟兵他们忙着写完稿子,又喊来两个处得兄弟般的球员,他们先到延吉最有名的一家狗肉店啃了几条狗腿,吃了许多根狗鞭,壮完阳后,他们搭乘两辆出租车直奔黄龙。迟兵后来告诉我,去黄龙那天是他最倒霉的一天。他首先遇到了一个如花似玉的朝鲜族女孩子,当他在包房里脱掉裤子开始做爱时,迟兵说自己忽然闻到一股臭臭的味道,这种味道有点象腥咸的烤鱼片儿,迟兵当即就阳痿了,他知道自己碰上江湖上臭名昭著的"臭眼儿"。迟兵正为鼻子边上的臭味儿发愁时,他又听到包房外边乒乒乓乓一阵乱响,还夹杂着女孩子的尖叫声。迟兵还没提好裤子,他就被两个穿着制服的人拎了出去,随后他们四个记者和两个球员,再加上八个女孩子,统统被塞进一个卡车上拉走了。
六个男人怎么出来八个女孩子?这不奇怪,迟兵他们四个记者每人一个,两个球员浑身是力气,他们每人叫了两个。在卡车上,有两个小子吓得开始发抖,迟兵转着脑子想着办法。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交完罚款就放人,可迟兵并不想让哥们交罚款。他想到延吉地面上一个很有名的哥们,他也是记者。迟兵问身边的警察能不能打个电话,警察瞥了一眼问,怎么?没揣足钱啊?迟兵这个时候很诚实,他说这帮人都是记者,来延吉采访比赛,到延吉实在闲极无聊才跑到黄龙来玩的。警察同意迟兵打电话,迟兵拨通延吉那哥们手机后,压着嗓子把事情如实说了,延吉的哥们真有面子,一个多小时后,他亲自开着车,拉着市局一个很有身份的领导,把迟兵一行六人安全接回了延吉。
从那以后,迟兵一提朝鲜族女孩子,就想到发生在黄龙的那个插曲。弟弟把唱歌的这个朝鲜族女孩子介绍给他时,迟兵还开着玩笑:"我希望她身上只有香水的味道,否则我会自杀的。"
我看到迟兵那种甜蜜蜜的样子,我真想马上找条烤鱼片儿揣进女孩子的口袋里,让他突然间能恶心起来。
我最初下楼送这帮哥们时,宁殊没有跟下来。
中午时分,她来到大堂里找到了我。我看到她时,我问她:"怎么下来了?睡好了吗?"宁殊淡淡一笑:"他们都走了吗?"我知道她是在问迟兵和老林他们。
"就剩下迟兵了。"我说,"他在那里正和朋友话别呢。"
宁殊向人群里看了一眼,她对我说:"我要和他打个招呼吧,然后我去吃饭。"
"你吃饭把我扔下啊。"我笑着说,"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起吃个团圆饭都不成?"
"你都要走了,不回家去看看你爸妈?"
"也是啊。"我说,"那团员饭我们就晚上吃吧。"
还是把我晚上的时间留给宁殊为好,我想。我决定下午回家去看老爸老妈。
"吃完午饭我再回家。"我对宁殊说,"多吃一顿是一顿了。"
宁殊轻轻一笑,她说:"吃一百顿有啥用。"
她向迟兵走过去,我随后也跟着,迟兵见我们过来了,他觉得我们是来催他。"不早了,不早了,是该走了。"他笑着对我和宁殊说。
迟兵脚下是两个大旅行包。我知道在某一个包里,装着五六个熏鸡架,就是把鸡的骨架用特制的原料浸泡好,然后用火熏熟,颜色黄润,味道醇香。熏鸡架也是沈阳著名的风味小吃。迟兵说他要给老婆买几个尝尝。在外边总做对不起老婆的事情,回家了给老婆买几个鸡架也算弥补一下内疚的心情。实际上,迟兵自己最爱吃这种东西,他常常买两个鸡架回房间,关上门后,满走廊里都能闻到那种香味,如果推开门,就会看到他的双手不停地撕扯着小小的鸡架,手上冒着闪量的油星,嘴巴和鼻子上也粘满肉沫。
沈阳的从事色情的鸡们聚集在西塔一带,老TMD好吃的鸡架则集中在市中心的八一公园附近。有好几次,迟兵从酒店打车到那里去拎回两三个鸡架,回来后老林和他抢着吃。迟兵对沈阳人发明熏鸡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没有创造力的人是难以发明熏鸡架的。同样,也是那些对生活和艺术有许多想法的人才喜欢吃鸡架这种玩意儿的。那些每天只想啃鸡腿,鸡胸脯,鸡翅膀,爱吃鸡疹,鸡爪,鸡皮,鸡头之类的人,永远是俗人,庸人或者废人。
迟兵的这套理论从他来沈阳第二次吃熏鸡架时就出台了。我记得他在八一公园大排挡边啃鸡架,边发挥着自己想象力,并扬言自己回上海后,可以让自己失业的小舅子开个熏鸡架店。他粗略地估计一下,一天生意好了能赚上五六百元是没有问题的。当时,高颖也坐在他身边,高颖甚至笑着说,一天要是能赚这么多钱,她就到上海主持小店生意去。迟兵满嘴应诺,并让高颖多从东北带几个姐妹去当服务生。我听到这里要笑,我想,这小子找服务生是假,他一定是想找些东北女孩子到上海卖淫,然后自己当鸡头了。
看到迟兵要走了,我无法控制去追忆在这断断续续的两三个月里,迟兵这个最好的哥们留给我的点点滴滴。迟兵叫来出租车的时候,那个朝鲜族女孩子也跟着上了车,看样子象是要送迟兵到机场。迟兵和我说了声:"哥们,走了!"然后和宁殊握手,笑着说:"有机会到成都一定回去看你。也希望你心想事成。"宁殊向迟兵点着头,只低声说了一句:"有缘份的话,还会见面的。"
当我最后一个哥们乘车呼啸而去的时候,我眼睛发热,泪水差点下来。
我知道,哥们都走了,身边剩下的只是一个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宁殊了。沈阳还有什么?我的老爸老妈?弟弟?或者说那个做了小媳妇的梅昕?
我觉得沈阳是一座空城,在这样一座空城里,我还要鼓足勇气陪宁殊最后走完10几个小时。
迟兵走后,我问宁殊吃不吃肯德基,她点点头。
我们随后顺着中华路向西走十几分钟,来到肯德基的一楼大厅后,我要了一听啤酒,两袋薯条,一个汉堡和一杯热奶。一大托盘的东西,只有那听啤酒是属于我的,其它的都是宁殊平时喜爱的食物。
我们找一个临窗的座位,我起开啤酒,先狠狠喝了一口。
"下午你也没有什么事情,跟我回家吧?"我对宁殊说。
"我跟你回家干什么?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还想买点什么带回去的。"
宁殊的回答没有出乎我的意外。她要能和我回家,那就奇怪了!
"你不知道买什么的!我下午给你买回来。你在房间里等我就行了。"
"你真的不要再管我了,我不是孩子,我也用不着你管了。"
宁殊手里拿着一根薯条,在番茄酱里一边蘸着,一边对我说。
"我是善始善终的人,你在沈阳一天,我不能不管你的。"
"你没有理由再管我了。"她把薯条放在嘴里,抿着嘴嚼着,"我们只是一般朋友了,你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的事情多了,所以我必须要管。"
宁殊听到这里笑了,"知道多有什么用?你知道一个人要把另一个人杀掉前说的是什么话吗?是这样的话--你知道的太多了!"
"这话应该我对你说的,因为你连我不穿内裤的习惯都知道。"
"别说的太脏了,我可不想听这些。"
"做都做了,听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嘟囔这句话时,心理竟然有重莫名其妙的反感。我知道宁殊的确很单纯质朴,可在我面前穿上裤子,不想再发生任何关系后,也不至于这么快连我的一句玩笑都就受不了啊!
脱光衣服时是荡妇,穿上衣服就成了圣女,女孩子也许都是这样。
我也想到我们报社文艺部有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子,她刚分来的时候和男孩子说话都脸红,夏天她站在男孩子堆里,眼睛看得最多的总是自己的领角短裙,因为她自己春光乍泄。可是她结婚两年后,她领着自己小女儿到办公室时,小女儿嗷嗷待哺,这个小媳妇竟然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拽出自己的乳房,把挺拔的奶头毫不迟疑地塞到女儿的嘴里。这是我在文艺部亲眼目睹的一个场景,那时,文艺部里一屋子的人,我看了一眼小媳妇拽出的乳房后,我心理诅咒,婚姻真TMD不是东西,它是如此容易地让一个女孩子失去了羞耻。
这也许就是真实的女人。
"我们不能再呆两天,非得明天走吗?"我想转移个话题。
我那该死的领导同意唐嘉到大连玩两天的时候,他也让我好好在家里歇几天,我也不想马上回成都,我和宁殊第一次说了这个想法后,她摇着脑袋拒绝了,我不死心,我想自己多和她呆一天赚一天了。
宁殊的立场没有变,她看着我说:"我明天一定要走的,我可没有拉着你一起走。"
"你一个人走我能放心吗?"
我想,她是死不回头了,还没等宁殊对我的话做出反应,我接着说,"那好吧,我也不呆了,明天我们一起走。"
宁殊没有说话,她只顾吃她的薯条。
看来我下午一定先要回家看看,早点回来陪宁殊。我很看重我和她在沈阳最后一个晚上。这应该是一个和狗屁足球没有多大关系的夜晚,酒店里没了狗仔队的身影,球队也要出发了,这座城市终于恢复了平静,我和宁殊只象两个普通游人,出入于酒店那个飘扬着淡淡香味的房间里,我躲在自己的房间,听着自己踩到地毯上猫一样的脚步声,看着宽阔得象天安门广场一样的大床,我会感到孤独吗?我会孤独得去敲开,或者干脆揣开斜对面宁殊的房门,然后和她拥抱在一起吗?我不知道。
68
我从家里回到酒店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我先回到自己的806房间,把老妈带给的两大包榛子和木耳放在屋里,老妈总认为成都没有这两样东西,每次我从沈阳回成都,她都要提前把这两样东西给我买来,装好后让我无条件地带走。
我把包放在房间里后,去敲斜对面宁殊的门。这两个房间欧阳至少还要用10几天,他们那个庆功晚会延期了,要等国家队客场打完乌兹别克斯坦后开,房子自然要等着晚会了。
欧阳想得也算周到,我白住了两个多月的房子,他和唐嘉临去大连前,给我扔下两张空白发票,让我回去自己去填。我可报销的房费应该在15000元左右,再加上为本溪李总搞那个轰轰烈烈的活动,欧阳按事先说好的比例分给我80000万,还有卖部分球票的收入,十强赛这两个多月,我粗略算起来有十万收入。我算到这里很得意,我想到我那可怜的大马,他辉煌地站在国家队的替补行列里,打完十强赛也就混个三五万吧。
我下午回家给老爸老妈每人一万元钱,他俩看着两叠钞票,追问钱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我看到老妈眼圈泛着红,告诉我不是正道来的钱花一分欠一分孽债,早晚要还的。我耐心地从本溪李总的那个满是粉刺的鼻子讲起,一直说到为他策划那个活动的深远影响,最后老爸老妈才把钱收起来。我当时含糊地对老爸说,闲时少喝点酒,多去做点保健按摩,老爸听到这里只是笑,从他那得意的笑里,我相信自从我和弟弟把他领到那家康乐中心后,他自己注定偷偷地去过多次了。
在我的计划里,晚上回到酒店后,我要请宁殊到万豪酒店去喝德国黑啤酒。选择万豪是因为它就在五里河体育场边上,又是沈阳最好的五星级酒店之一,十强赛客队来沈阳比赛,大多住在万豪。我想拉宁殊在那里坐坐,喝下几大杯特酿啤酒后,迷迷糊糊里我们能最后疯狂一个晚上,可这个计划在我敲开宁殊的房门后落空了。
宁殊倒在床上看着电视。她的旅行包在窗口的沙发上,收拾得整整齐齐的。画夹放在写字台上,上面放着一个大的塑料袋子,那里好象是她在街上买的东西。
我让宁殊起来去走走,宁殊摇着头。
"最后一个晚上了,呆在床上多没有意思。"我说,"我们到万豪听歌去吧。"
宁殊还是摇头。我伸手拽她,她把手抽回去,"真不去,早晨还起早,经得起折腾嘛!"
"也好。"我看一眼宁殊,走到写字台左侧拉开冰箱,"这里没有什么了。我去买点东西,我们在房间里吃宵夜吧。"
"我可不吃什么了,你是不是找下酒菜啊,我下午买了一些。"宁殊用手指着窗台的方向,"在那里呢,你去闻闻,没有什么味儿吧?"
有没有味儿都无所谓,的确,我的想法就找个喝酒的借口而已。
我把两个房间的冰箱的八听啤酒喝下去时,宁殊手里的那瓶蜜桃汁只喝到一半。我开始觉得脑袋发沉,重重地向下坠。我只记得电视里还在演着美国人抓拉登的故事,宁殊先是瞪着眼睛看,后来看到我挪着屁股坐到她身边,她向后动动,身子靠在床头。
我拽过宁殊的手,"你真要永远生我的气吗?"我的声音很轻柔。
她的手没有动,她看着我说,"我谁的气都不生。"
我床边的屁股滑到地上,宁殊想拉我一把,可我已经坐在了地上。
我继续拉着她的手,挪挪身子,两个膝盖跪到地上,脑袋搭在宁殊平伸着的左腿上,屁股微微地撅着。
"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想失去你的。"我嘴里呐呐地说。
宁殊突然笑了,"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子可不大的。"
她好象从我跪着的姿势和虔诚的语言里察觉到什么,她拍拍我的肩膀说。
"我们真的一点希望没有了?"我抬起头问她。
"我早就说过了,别这样折磨自己和别人了,好不好啊?"
宁殊的话里带着一些不耐烦的味道。我站起身来,强行把宁殊压在床上,嘴里说:"我真的离不开你,真的,真的……"
尽管脑袋涨涨的,我的神智还是很清楚的,我说这样的话只是想让宁殊重新接纳我,这种接纳应该是从理论上接纳,好象和情感没有多大关系了。
我的身体死死地压着她,我内心里有性欲要来前的那种躁动不安,可是我的小弟弟软得如面条一样,它没有承袭我身体的重量,进而硬硬地去挑衅宁殊。
宁殊在我身下挣扎两下,最后象是对我下最后通牒:"下去!再这样我真喊人了!"
她对我说第二遍的时候,我从她身上下来了。我不想惹怒宁殊,我知道在沈阳的最后一夜,我与她做爱的唯一方式就是强奸她,可我连强奸她的力气好象都没有了,我和她的情感真的走到了尽头?
我后来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想做的就是尽快能够成功地手淫,让小弟弟嘴的唾液都吐出来。我释放一下自己,也许就不再去想着宁殊了。
房间的窗帘被我紧紧地拉上,我动了八九分钟,小弟弟没有一点抬头的欲望,我有点气急败坏地在房间内走动,象得了多动症一样。这时我突然想到谭菊,我希望她的声音能刺激我一下。
"你怎么还不睡觉?宁殊呢?"
谭菊接到我的电话后,吃惊地问我。她的话很轻柔,象是睡觉前的那种躺在枕头上发出的声音。
"她在那个房间。我睡不着觉。"
"你明天还要其早的,都几点了,能起来吗?
"你过来吧,我真睡不着。"
"都快到凌晨一点了啊,门都出不去了。"
"不过来了?那你想我了吗?"
我也没想让谭菊过来,我和她说话时,手一直在动着小弟弟,任凭我变着花样来动,小弟弟立场坚定地疲软。
谭菊曾说过要到机场送我们,我后来没有同意。宁殊已经知道了谭菊和我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谭菊出现在机场,显然会让宁殊更尴尬。谭菊后来赞同我的想法,她只是告诉我到成都后给她打电话。
我和谭菊在电话里聊了两三分钟,我气喘吁吁,我也有点绝望了。
我靠在床上,嘴里呐呐地说着什么,我真的记不清自己说了什么。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过去喝多酒的时候,我遇到过这种状态。
谭菊在大声喊我,我听到她的声音。谭菊用我老妈一样的语气对我说:"真的,你快去睡觉吧,你都坚持不住了,刚才都说梦话了。"
我知道自己一定说梦话了,但我不会承认。
"不可能,一定是你听错了。"
"什么错了?你刚才说什么--我不考,我不想考啊--你说了好几遍。"
TMD!我刚才处于半昏迷状态时,一定又面临着数学考试了。谭菊不知道我这个习惯,我听到她重复我的梦话后,我笑着对她解释,"那是黄嗑儿,我是说我不靠啊!你还不知道嘛,我阳痿已经好长时间了,我没有能力靠的……"
"让我依靠/让我靠/没什么大不了……"我想到这句歌词。这么一个夜晚,谁让我靠?我不争气的小弟弟又能靠谁?在谭菊面前,我只能拿自己来开玩笑了。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世界杯短信游戏多多:点球大战、足球经理、世界杯大富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