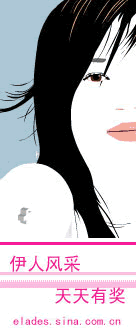|
61
国家队以1-0战胜了阿曼后,我在欧阳停车的地方见到宁殊时,她泪流满面。我看到她这种动情的样子,搂着她的肩说:"亲爱的,控制点情绪,不就出个线嘛!"
说这话时,一群西安的球迷赤裸着上身,几十个人搭着肩,迈着铿锵的脚步,喊着口
号向五里河北门的方向走着。此时的体育场外,鞭炮齐鸣。这群西安球迷走过我们的身边,他们那些被火光与硝烟中泛着油光的臂膀,死死地扣在一起,再加上他们整齐的步伐,我想到鬼子进村时的情景。当然,这些人中,大多数脸都挂着晶莹的泪水,宁殊看到这些一个个壮烈的场面不能自己,我看到她的眼泪又哗哗地流下来。
拄着双拐的韩桅也一直在哭,她哭得更直露一点。宁殊哭时可以偶尔用手去擦擦脸上的泪水,韩桅却不同了。她的两只手紧紧地扶着拐杖,稍一大意,随时都可能被拥挤的人群撞摔在地上。韩桅只能任凭泪水滚落在地上,脸上保留的是一种充满幸福的笑容。
我知道,她们都是为中国足球哭的。球迷热爱足球,就象虫子热爱苞米,那种纯真朴素的情感只有自己知道。在这样一个恢弘躁动的氛围里,任何泪腺发达的人,也许都会被刺激出眼泪,这也包括我自己。当十多束礼花映红体育场东面的天空时,我看到礼花下面一张张涨红的脸膀,看到宁殊和韩桅的样子,泪水在我的眼角里打转儿。只是,我的泪水和国家队出线与否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完全是一种生理刺激而已,就象你漫不经心地走进火葬场,你看到那么多素昧平生的人呼天抢地的,你要不被弄出眼泪来,只能说你是一块石头。
活动的展台全部运上卡车拉走之后,已经是比赛结束后一个多小时了。
欧阳最后用自己的车直接把李总送回了宾馆,我们一帮人坐上欧阳公司的那台中巴,绕上大二环拐进市区,最后回到了商贸饭店。
回到我的房间后,我让迟兵把要发稿件的哥们都喊来,晚上要发稿,我们事先准备好的稿件必须要送到他们的手里。
"各位今晚要多费心了。"我说:"我们准备好三类稿件,一会儿发给大家,争取明天见报。"
有两类稿件都是我亲自来写的。一类是评论,一类是特写。另一类则是图片新闻。我炒作这次活动依照的基本原则是早已预谋好的,那就是以道德悖反为宣传主线,比如,厂家的一次社会公益活动,由于球迷素质原因,饮料盒扔得遍地,体育场变成了垃圾场,再有,一些展台被球迷毁坏,展台上的石英钟也不见踪影--这样的话题绝对是新闻炒作的由头。
"稿件的字数有没有要求?"一个哥们问。
"评论不到七百字,压缩字数恐怕会破坏中心思想的。特写的字数可以删减些的。"我说,"至于图片,本来是摄影报道,文字说明不足二百字,字数再少的话说不明白的。"
"弄两篇可以吗?"关雷很认真地问我,"再有,国家队出线的这种喜庆的气氛里,我们弄个质疑球迷素质的文章,会不会都被领导们给封杀了?"
"任何一个成熟的媒体,都不想只唱赞歌的。有篇与众不同的稿件,这才是水平。"我告诉关雷:"你觉得一篇东西可能发不上,也可以往你报社发两篇东西,一个言论,一个图片,这至少能保证发一个嘛。"
稿件很快被分发下去。许多哥们还肩负着二传手的作用。老林除了自己的报纸上要发稿,他还要把我们的稿件传给珠海和广州两家报社。我们许诺李总的全国发40家报纸,这个数量有一部分是靠象老林这样的二传手来完成的。
李总对在辽宁当地发稿比较看重。他要求除了沈阳和大连外,其它小市的报纸也都要发稿。我把这个认为交给了陈超。早在他求我忙着弄论文集时,我已经把这个活动要在辽宁发稿的事情透露给他了。房间里的哥们都走后,我拨通陈超的手机。
"活动顺利完成了,稿件我发到你信箱里?"
"发过来吧。这么晚没有动静,我以为不搞了呢!"
"你和各个市的报纸打招呼了吗?"
"还用打招呼?比赛的稿件他们都跟我们晚报要,我顺手把活动的稿子交给他们,谁敢不发啊。"
"除了你的劳务费1000元,其它城市每篇稿子200元可以吧?"
"可以,可以,给他们点就行的。"
我知道辽宁的另外十几个小市,每篇稿件的200元钱,陈超不可能送给发稿者的。送不送我是不管了,反正我已经从每篇稿子的1000元给他降了800元,这笔额外收入正好算做我、唐嘉和迟兵出论文集所应交的费用。
我布置发稿的时候,宁殊也不插话,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里那些球迷狂欢的画面。她看到我完成任务时,转过头来看着我。
"我们去市政府广场吧?电视里说那里有20多万球迷!"
"等我写完稿吧。"我笑着说,"快到11点半了,我一个字都没写呢!"
"你写完稿,黄瓜菜都凉了。那我自己去了?"
"亲爱的,你别开玩笑了,外边这么乱,你被人拐跑的话,我还得去找你。"
"哼!"宁殊用鼻孔抗议我一下,"你写你的吧,我回我房间看电视了。"
她说完站起来想走,我一把按住她。
"你就在这儿看嘛!我很快的,写完了我们就去上街。"
宁殊坐下来。我说:"看电视时可不要再哭了。你一哭,我一个字都写不下去的。"
"去你的吧!"宁殊瞪我一眼,"你以为我是为你哭啊!"
"可我希望你为我哭的!"
"还贫?你快写稿吧!"
我满脸堆笑地应诺着。可是心里象长了草。我们报纸截稿是凌晨,写稿是来得及的。再说唐嘉看完球后就开始忙稿件了。我坐在房间里想的是,斜靠着床边的宁殊,她为什么不象以前一样绻卧在我的怀里,为什么在这张我们已经熟悉的床上,让我变得如飘在空中的云雾一样,始终在这样的夜晚找不到根的感觉?
我嘴里说着自己要整理整理思路,我凑到宁殊的身边,拽过她的手,她没有拒绝。我又去搂她的间,她闪了闪说:"哎呀--又要干什么?快去写稿啊!"
"我也挺激动的。毕竟我们进了世界杯了。"我说。
我尽量说宁殊愿意听的东西。进不进世界杯关我屁事。
"我可没有看出你兴奋来。"
"我的爱是深沉的,能和你们小孩子比嘛!"
"那是深沉?"宁殊笑着说:"是麻木吧!"
"没办法,"我叹口气,"看来你真是不理解我了。"
我说完,使着劲儿把宁殊揽在怀里。她出乎我的想象,顺势把头枕在我的腿上。我用手捋捋她的头发,然后又轻轻地摸着她的脸庞。
"其实,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兴奋不起来的。"我说,"从南京回来后,我心里一直都很难受的。我是看到你难受的。"
"我可没想折磨你的。"
"不是你折磨我,是我自己折磨自己。"
"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自己也有点糊涂,你从南京回来后,我对你的依赖敢好象比以前大了。比如,看不到你,就觉得整个饭店里一个人没有似的。"
"我可比以前轻松多了。"宁殊嘿嘿一笑,"还是欲望不要太强好。"
"可我们都不是没有欲望的人啊!"
"我现在就是了。"
"我不信!"我说完,搬起宁殊的头,热烈地吻着她。
宁殊仍然先是有点反抗,后来不由自主地和我配合起来。我吻她有四五分钟,抽出搂着她肩的手,把她放倒在床上,我趴在她身上,嘴在她脖子附近不停地蹭着,伴着粗气。
"亲爱的,我受不了了!我想要!"我喃喃地说。
"不行,不行的。"宁殊摇了两下头。她的手还搂在我的背上。
"我真的不行了!"我是有点不行了,我觉得自己两腿之间好象夹着炙热的炸药,导火索已经哧哧地响着,爆炸马上就要发生了。
"亲爱的,那……你动动我吧。"我说。
我把宁殊的手拽下去,放到我短裤口处往里塞。宁殊要抽回自己的手,我强行让她的手摸到已经有些发湿的小弟弟时,她开始慢慢地动着它了。
小弟弟在宁殊的手里跳跃着。她坐起来,我平躺在床上。也许是累了,宁殊不停地换着手,最后用一种焦虑的眼光看着我的上身在床上一张一合的。我偶尔看到她也不时地皱着眉头,几缕垂到嘴角的头发被她的粗气推的忽忽悠悠。
宁殊突然停了下来。
她耷拉着脑袋,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怎么了?亲爱的?你别停啊!"我死死地盯着她。
宁殊忽然解开衣扣,脱掉上衣,接着又去拽自己的裤子。她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和一件背心时,她抓起床上的外衬,甩到下面,然后钻进白色的传单里。
"我受不了你这个样子的。"宁殊的脑袋露在被单外边,她看着我说:"来吧,今天我也挺高兴的,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在乎这一次。我给你!"
62
梅昕要结婚了。
梅昕打电话告诉我她要结婚的酒店,我说,妹妹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准时到的。
上午十点多钟,迟兵、老林和关雷在酒店大堂里等我。谭菊也知道梅昕结婚,我问她时,她说要在中午下课的时候才能去。我关好房门时,走到宁殊的房间时,按响了门铃。宁殊还没有起床,她穿着那件露着肚脐儿的小背心,给我打开门后又钻回床里。
"我一个朋友结婚,我要参加婚礼去。"我没说是梅昕结婚。
"没事儿你不会起这么早的。"宁殊嘟囔一句。
"少喝点酒。你看你这两天喝的。"
我笑了笑,用手摸着她露出床单外的胳膊,又伏下身亲了她一下。
也许好几天没怎么吃主食了,我看到床头柜有两个煮鸡蛋,顿时来了条件反射,肚子竟然咕噜骨碌地叫了起来。我拿起鸡蛋,迅速敲碎,剥光皮后把整个鸡蛋塞进嘴里嚼巴嚼巴咽了下去。宁殊看到我这个样子,她欠起身,把另一个鸡蛋剥好递给我。
两个鸡蛋好象没有经过胃来消化,直接滚到肛门附近了。我站起身,觉得小肚子涨涨的,有一种强烈的排泄欲望。我四处张望一下,我和宁殊要纸。
宁殊笑着说:"你啊,早知道这么快去厕所,你还不如直接把鸡蛋扔到厕所里去呢!"
"是啊,是啊!"宁殊的话让我忍不住笑起来,我一边猫着腰向厕所里跑,一边应酬。
蹲在厕所里,我想起梅昕。梅昕要结婚了,她以后真会变成一个良家妇女?会变成三四年前那个单纯的女孩子?一个很许多男人睡过觉的女孩子想要单纯,除非她是植物人。我想,梅昕只有好好过自己的日子,真象几年前我为她设想的那样,用自己积攒的钱开个服装店,或者花店?
我唯一感到内疚的是,我让她替谭菊承担了莫须有的责任。面对受了委屈的宁殊,我指着身上的印记说出梅昕名字的时候,我有种出卖自己灵魂的味道。多年来,尽管梅昕那张可爱的面孔也多次撩拨过我,我却以不与她做爱来固守着道义的最后一块阵地。可是,我混淆是非,从精神上侮辱她,这难道不比做爱还无耻?
梅昕在迟兵和老林他们面前的那种从容,有时候让我觉得可怕。那是一种看破红尘后的麻木,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生活方式?但这也许是男人最需要的。
男人们都希望把想甩甩不掉的女孩子培养成一个风骚放荡的人。女孩子风骚放荡了,男人才能在道德或者责任的夹击中成功突围。梅昕这样的女孩子不会让让男人们有突围之苦,宁殊有吗?当她最初来沈阳时,她萌生要和我结婚时,我尽力用自己的老婆来搪塞她,我也没有想让她掉进荡妇的荡妇里。换句话说,宁殊现在对我谨慎的肢体接触,常常让我欲火焚心,可我也塌实许多,她毕竟不会因对我的失望去放纵起来。
我多少也有点迷惑,比如那个夜晚,那个她"也不在乎这一次"的夜晚,我魂销魄碎。我后来希望她在沈阳的有限的日子里,每天都能不在乎一次,可宁殊足球出线那天晚上后,坚决地恢复了在南京时的承诺。我只能去亲她,去拥抱她,宁殊的裤子再也不能随便脱了。
我清醒的时候想,宁殊那天晚上肯脱光自己的衣服,她那白皙的肉体里散发出的情感是简单,还是复杂?难道在那样一个夜晚,任何一个铁杆女球迷都有一种献身精神?
我只能把那晚上宁殊的行为,看成是他的另一种纯真。在马桶上,我只能这样想。
梅昕结婚在兰花宾馆的三楼餐厅。
我们到达三楼时,宴会厅里已经挤满了人。梅昕穿着一身浅绿色的婚纱。她看到我们时,小跑着迎上来。我看到她描着淡妆,粘着假睫毛。梅昕甜甜地一笑,那长长的睫毛不停地颤抖着。
她身边穿着整体西装的男子当然是新郎了。他中等个子,长着一张憨厚的脸。他听到梅昕一一介绍后,微笑着和我们握手致谢。
"就等你们了。"梅昕拉着我的手说,"宁殊呢?她怎么没有来啊?"
"她昨天感冒得很厉害,起不了床了。"我编个理由。
"哦,是这样。"梅昕说,"哥,你当我证婚人吧,我已经和主持人说了。"
梅昕的话吓了我一跳,我说:"别,别,别啊。我没当过的,换别人吧。'
"就是念念结婚证书,走走过场的。你不肯当我就生气了。"梅昕撅起小嘴。
新郎也笑着对我说:"大哥,你就别客气了,小昕总提起你,你就答应她吧。"
我向梅昕点点头。我也很不自在,梅昕拉着我的手时,我感到脸有点发热。新郎会怎么看我,看我身边的迟兵和老林他们,都是嫖客?新郎或许会想。
婚礼共有二十多桌。大家都落座的时候,在主持人洪亮的嗓门里,我上台宣读了新郎和新娘的结婚证书。从台上走下来的时候,我看到除了三四桌双方家属外,其余的都是年轻人。女孩子至少有五六桌。我坐到迟兵身边时,他笑嘻嘻地看着我。
"当证婚人是什么滋味?"
"味道好极了。"我说,"有种橄榄的味道。"
迟兵笑得很阴险,他低声对我说:"我总觉得有点胆突突的。"
"为什么?"
"谁知道了!总怕谁一酒瓶子冷不丁砸在我脑袋上。"
老林也悄声说:"可以理解的。你看看,这屋里的男的哪个不象嫖客?"
我瞪了他一眼:"都是嫖客的话,是不会有情敌的,有什么可怕的。"
老林在旁边嘟囔着,"女的都象妓女。"
我瞪他一眼,"别瞎说话了,我们是把梅昕当朋友,然后才参加她婚礼的。"
关雷只看着我们嘀咕,他一句话不敢说。他身边坐着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谁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关雷也想和迟兵说话,迟兵忙着和我搭讪,关雷面部表情木讷,我甚至看到脸上肌肉不停地抖动着。
这也够为难他的了。梅昕只给我和迟兵打了电话,我后来把老林和关雷都喊上了。做人有时是为一个面子,我想多拉两个人给自己和梅昕都撑撑面子。关雷听说参加梅昕的婚礼,在房间里就有点怯场了。老林连骂带损,对着关雷喊:"人家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梅昕陪过你,还没超过一个月,你怎么穿上裤子就忘了感情了?"老林的话把关雷的脸弄得白一阵红一阵,最后他自己找台阶下:"我也没说不去。哪个做贼的不心虚?"
我左边的位置是空着的。这是我给谭菊留的座位。
谭菊快到中午12点时来了。她站在餐厅的门口四处张望,不知道我们坐在哪个桌子旁。我把她叫过来,谭菊坐下没有几分钟,梅昕利用在临桌敬酒的间歇来到谭菊身边,搂着她的肩说:"菊姐,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想死我了。"
谭菊站起来看着梅昕的一身打扮说:"做小新娘子了,真漂亮。"谭菊一边说,一边用手摸摸梅昕头上的发型,"很古典的,象仕女的发型啊。"
她怎么想到侍女的发型?"谭菊啊,你说话可要小心啊。"我心里想。你要说发型象秦淮河边上的妓女杜十娘的话,还不如直接骂梅昕了。
"是吗?我可没有她漂亮吧。"梅昕格格地笑。她也许不知道侍女是什么东西。
梅昕和谭菊打个招呼后又忙着敬酒去了。谭菊坐下来。她叫了一声饿坏了,拿起筷子不停地向嘴里送着东西。
"下午有课吗?"我问她。
"后两节的。"
"一会儿跟我走吧。"我趴在她耳边说:"很想你,回来后也没有和你好好聊聊。"
"哼,没好事!"谭菊看了我一眼,她问我:"宁殊你俩怎样?"
"还那样。她立场坚定着呢!"我笑着说。
谭菊笑了笑。她伸起腰,满屋子张望里几眼。婚礼这个时候已经达到了高潮。到处是喧嚣的声音,还伴随着酒瓶子撞击的动静。在我们右侧的那几张桌旁,几个年轻的小子涨红着脸,端着杯子正和一桌子的女孩子拼酒。几个女的拎着瓶子,扯着嗓门和男人们大喊大叫着。其中一个打扮有点妖冶的女孩子,一只脚踩着凳子,扬着脖子把一瓶啤酒咕噜噜地往嘴里倒着。
谭菊到来之前,我告诉迟兵他们几个不要瞎说话。我说,谭菊一直不知道梅昕的真实身份。在这种火暴的婚礼上,谭菊看到男男女女这么动情地用酒撒野,她完全可以认为这是梅昕的同学,或者同事们热烈的捧场。但我是看出来了,那几桌疯狂地灌酒的男女们,那种恣意和张扬,绝对象发生在有黑瓜子和开心果的昏暗的包房里。
喝下去几杯酒后,关雷的胆子好象大了一点。他踱到我身后,轻轻地拍着我的肩。
"你看那桌--穿黑衣服的那个女的是上次陪我的。"
关雷想和梅昕睡觉被婉拒时,我曾让梅昕另给他过别人。看来当时梅昕找的就是那个桌上的女孩子。
"她也很有福气啊,能听到你唱流行歌曲!"我挖苦关雷。
"靠!她可比梅昕差多了。"
谭菊见我和关雷蛐蛐咕咕的,她侧过身来问我:"怎么了?说啥呢?"
"关雷说他在大街上见到过那个桌子上的一个女孩子,我让他去敬酒,他不敢。"
"没看出你胆小啊,去敬呗!"谭菊也逗着关雷。
关雷尴尬地在我身后笑着,"我才不去呢!"然后他迈着方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谭菊见关雷走了,她捅了我一下,"我一看到梅昕有点内疚,我的事情不该推到她身上的。"谭菊问我:"梅昕是不是不去你们那里了?"
"是没去啊。活动都结束了,也没有事情。"我说,"她还要忙自己的婚事的。"
"一定是你告诉她不要去的。"谭菊白了我一眼。"我总觉得心理不太舒服的。"
谭菊的心情我能理解。面对宁殊的责问,如果让她选择坦白的方式,她一定会告诉宁殊那个人是自己。
我们在梅昕的婚宴上呆了一个多小时,我不太习惯这里的氛围,迟兵他们也很难放得开。梅昕给我们这桌敬完酒,我们塞了红包给她,坐了一只烟的工夫,我先站起来,看着梅昕在另外一张桌子上点烟,我向外比划比划,示意我们要走了。梅昕走过来让我们再等等,她说还没有好好和我们喝酒呢。我笑了,我告诉梅昕下午还要采访,我们必须得走了。
关雷在我身边微笑着听着我们说话,眼睛却盯着梅昕的乳房。她的两个乳房在薄薄的婚纱里,随着她不停地说话而颤动着。
"哥,比赛也都快结束了,你们也该走了,哪天我们去看你。"梅昕有点眼泪汪汪的。
她说完,从新郎手里拿过一个鼓鼓的红纸包,递给我说:"这个给宁殊带回去吧,要问她好啊!"
梅昕的"我们去看你"这句话,多少让我有点安慰。她有家了,不再是游仙,出门在外带着丈夫,这对梅昕来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我的这种安慰有时候让自己也纳闷,这么多年来,梅昕那张俊俏的脸庞永远定格在我和她第一次见面里。那时她单纯得象朵花,我在这样的一朵花面前,打扮得象她身边的伟岸的大树一样。任凭这棵树上落满乌鸦,钻满蛀虫,或者说根须一点点脱落,我却不忍心在她面前缩小自己的高度。她后来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混日子,我也常常把她当成值得信赖的商品推销给朋友们。此时,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把自己的行为仅仅看成一项皆大欢喜的公益活动而已。我脑海里的梅昕,依旧是我初识的梅昕。这也有点象雷锋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二十几岁的优质的小伙子,尽管他现在活着快到九十岁了,或者他活到三十岁就变成一个抢劫犯!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世界杯短信游戏多多:点球大战、足球经理、世界杯大富翁!
|